【闽南掌故】晚年禅居闽南的弘一大师发出“念佛不忘救国”的铿锵誓言
发布日期:[2024-08-23] 阅读人:1637 字号: 晚年禅居闽南的弘一大师爱国之心不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念佛不忘救国”的铿锵誓言
亭亭菊一枝 高标矗晚节
晚年禅居闽南的弘一大师爱国之心不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念佛不忘救国”的铿锵誓言
□林长红 文/图
核心提示
弘一大师(李叔同)是近代一位“抱热心救国”的爱国高僧。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组织“同盟会”,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成为“操南音不忘其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这位南社旧侣“标劲节,树清风”,抒写家国感怀,把自己的境遇同祖国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先后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其中《感时》《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等诗词,情真意切,慷慨悲歌,表达诗人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所写《我的国》《大中华》和《祖国歌》等爱国歌曲一度风靡大江南北。晚年禅居闽南的弘一大师爱国之心不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念佛不忘救国”的铿锵誓言。
弘法忧国 悲愤高歌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不断扩大,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佛教界弘法近二十年,佛学思想臻于成熟的弘一大师,于1937年2月驻锡厦门南普陀寺。曾将外出见闻之感想书示弟子高文显居士:“一、余买价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双,店员仅索价七角。二、在马路中闻有人吹口琴,其曲为日本国歌。三、归途凄风寒雨。”弘一大师这几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其中二、三两事,似乎令大师心绪难以平静。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军国主义者派遣大批浪人,自台湾跨海,混迹厦门等华南城市收集情报,为大规模侵略中国,鼓噪喧嚣,寻衅滋事。大师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时局和民族危机的深深忧虑,衬托了他彼时彼地的悲愤情绪。

《弘一大师全集》和《弘一法师驻锡泉南墨宝拓片集》等纪念书籍
1937年3月,弘一大师移锡厦门万石岩,但他的心情似乎格外沉重。他在《佛教公论》五月号上登载《释弘一启事》:“余此次至南普陀……近因旧疾复作,精神衰弱,颓唐不支。拟即移居他寺,习静养病。若有缁素过访,恕不晤谈;或有信件,亦未能裁答。失礼之罪,诸希原谅,至祷。”然而,正在谢绝外界访问与通信的弘一大师,却于5月初欣然应允厦门市政府的邀请编撰会歌。大师感时伤乱,心潮澎湃,写下了《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狓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见《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弘一大师巧妙地把强壮体魄与抵御外侮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运动会的主题歌,使整首歌曲高昂奋发,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深深地鼓舞了厦门全市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
1937年5月,弘一大师还应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诚请,北上弘法。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此时,北方局势异常紧张,有人劝请弘一大师速南归避险,但大师却愤然亲笔书写“殉教”横幅以明心志,并跋语“……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见《弘一大师全集》第七册)。同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又一次升级。中秋节后,弘一大师路经上海返回福建。他到上海后,夏丏尊及诸旧友到旅馆看望他。也许是大师有感于战争岁月里的人生无常,特意到照相馆留下一影。看着照片上那淡定的微笑,平和的神采,慈祥的颜容,谁也没想到,这一帧影像是在炮火连天的境况下拍摄出来的。人们后来把弘一大师这帧富有传奇色彩、兼具艺术家儒雅气质和佛门中人悲悯神色的慈影作为标准照,广为流布,成为20世纪中国经典的人物影像之一。

弘一大师纪念文集
大义凛然 晚节香劲
此时的厦门已是战云密布,敌机、敌舰常来骚扰。由于驻守厦门的国民政府海军力量薄弱,致使日本海军于1936年6月起不断到厦门“操演”“访问”,得以肆无忌惮地进出厦门港口,窥探军情,处心积虑地谋图占有厦门。同年7月间,日本第十三驱逐舰队司令西岗茂泰率领“吴竹”“若竹”两军舰窜进厦门。1937年9月3日,有三艘日本驱逐舰和一些飞机袭击厦门机场、炮台。1938年4月间,日本军舰相继又到厦门沿岸地区骚扰、炮击。其时厦门岛上硝烟弥漫,伤亡严重,日本侵略者对厦门军民欠下了一大笔血债。
据《越风》文史半月刊主编黄萍荪晚年回忆文章《弘一大师口述〈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提到,1938年4月,侵华日军舰队司令因久闻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往鼓浪屿日光岩寺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大师坚持“在华言华”而拒之。司令说:“吾国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何竟忘之?”大师以华语回之:“贵国为吾负笈之邦,师友均在,倘有日风烟俱净,祥和之气重现,贫僧旧地重游,谒师访友,以日语倾积久之愫,因所愿也。”司令又说:“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大师毅然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大师直面强敌,镇定自若,虽只简短数语,却浸透着大师的人格力量,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嗣后,一些中外报纸均冠以“爱国高僧”的标题予以详细报道。弘一大师平生推崇灵峰大师的诗:“日轮晚作镜,海水挹作盘。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愧,尘劫愿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大师在给弟子信中附录这首诗,借以表明自己此时的立场。
1939年农历十月廿五,弘一大师在永春普济寺时致徒孙郑健魂的信中写道:“……对付敌难,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曾与传贯师等言及。古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要紧,愿与仁等共勉之也。”而后,大师在祝贺南闽耆宿转道老和尚七秩寿联还写道:“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并在录写唐代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句时改为“人间爱晚晴”以自励。这里的“爱”既是佛法的慈悲境界,也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愫,以明自己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永葆心志节操,大师遂自署“晚晴老人”。

弘一大师在净峰寺作联自励
笃行明志 共纾国难
1937年农历九月廿七,弘一大师从青岛湛山寺冒着炮火回到厦门万石岩,随即大师要求安居在中岩石室,因为据说此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读书处,地势幽清,与万石岩毗邻,也便于了解外界的事情。据其弟子高文显回忆,此时的弘一大师常常失眠,于是听钟声而念佛,并多次在中岩开讲律学。随着厦门战局日益吃紧,缁素弟子为大师的安危而焦虑,劝请大师避入内地。大师却说:“为护法故,不避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并自题所居为“殉教堂”,表明自己誓与危城共存亡的决心。直至厦门岛陷落敌手的前四天(厦门沦陷为1938年5月13日),大师才离开厦门到漳州弘法。1938年农历五月十一,大师致弟子丰子恺的信上写道:“……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时逢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国运衰微,哀鸿遍野。同年初夏,弘一大师卓锡泉州承天寺。一天早晨,大师在食堂用膳,当时之际,禁不住潸然泪下,十分沉痛地告诫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泉州古称)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见叶青眼《千江印月集》)弟子们顿时泣不成声,异常悲痛。在此之后,大师每有开讲,座位后面的墙壁上总悬挂着自己亲手书写的横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题记说明:“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见弘一大师《抗日战争时期在承天寺书联》)此策励警语透露出弘一大师忧国忧民的感情,也体现了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态度。虽然,此时的弘一大师并没有脱下僧袍换成战袍,但他却能把佛法真谛与抗战救国有机地联系起来,赋予佛法以壮怀激烈的时代精神。他的宣讲佛理,既是一种觉世救世之举,也是在号召抗战。弘一大师将这种精神体现在每一件书法墨妙中,日书百幅救国联语,分赠各方,勉勖诸佛弟子共赴国难。
1938年冬季至1941年3月,泉州遭受了日寇飞机接连几十次的狂轰滥炸,死伤频闻,损失极为惨重。弘一大师时居泉州,当时“温陵处战事最前线,当舰队出入,飞机轰炸之际,公乃于此时独往独来,集众演法开示,不但置一己生死存亡于度外,抑且万一不幸,以头目脑髓替代众生受苦,亦所甘心。”(见叶青眼《千江印月集》)弘一大师对日寇的野蛮暴行非常愤慨,他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因此,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当时的晋江县佛教徒联合组成“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见庄荣标《雪鸿录》)。队部设在开元寺准提禅林,选拔爱国爱教壮健僧众教徒集合编训,学习护理知识,参与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为战时的泉州做出了佛教界的贡献。
弘一大师于1941年秋禅居晋江福林寺,该寺地处海疆前线,日寇军舰常游弋于永宁深沪湾海域,强敌压境,战事在即。泉州开元寺住持转道老和尚为了大师的安全,特派传贯法师前往劝请他回城避难。传贯法师带去一束红菊花聊作慰问,大师接物后有感于怀,遂托意《为红菊花说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道应流血!”表达了在敌人气焰方张之时,临危不惧,以民族大义为念,决然奉教的志向,这与其所主张的“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的爱国思想是相吻合的。

1938年10月,安海绅商学界欢迎弘一大师(前排中)莅临水心亭留影纪念。

1938年10月,弘一大师在安海题写“最后之胜利”。
著名学者朱光潜曾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佛终生说法,都是为了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确实,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表现出的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下救世的热血与肝胆。1938年10月,弘一大师在安海水心亭澄渟院时,赠予年轻学子李明信墨宝,所书“最后之胜利”五字铿锵作响的预言,委实意味深长。既鼓励人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也紧跟时局的中心任务,即抗战时期的口号是全国各地不论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奋起抗敌,争取最后之胜利。大师虽然只在安海弘法,但面对烽火弥漫的中华大地,不仅没有悲观失望,而且满怀希冀,深知为救亡图存而反抗强暴乃是必经大道,祈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一大师来不及亲眼看到抗战的“最后之胜利”,就于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安详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护生济世 激励来者
弘一大师曾发愿“为宏律而尽形寿”,但时代的风声雨声并没有使他完全忘情世事。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保持民族气节,积极宣传抗日,激励和影响了许多佛教徒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如亲近大师的僧俗弟子寿山法师、黄福海等人均为中共闽中地下党员,大师的弟子妙莲法师、广空法师、广德法师数年后为中共泉州地下党游击队筹集一百两黄金作为经费,为迎接解放大军早日进军福建做出重大贡献。1939年,弘一大师六十寿诞时,曾与大师年轻时一起“标劲节、树清风”的南社老友柳亚子寄来贺诗,诗后有两句“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与弘一大师共勉,寄寓了爱国文人志士与汉奸卖国贼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0年元旦,时年61岁的弘一大师特意书录《华严经》句:“身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寄赠老友夏丏尊。弘一大师自出家后,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说法传经,呵护生灵。曾与高足丰子恺策划编印《护生画集》,提倡护生,启示人们应有仁人爱物之心。凡依字典部首写经文时,总因刀字部多有杀伤之意而不忍下笔。但此时直面日寇种种暴行,弘一大师认为,今国人惨遭浩劫,抗战拯救生灵于涂炭,正是佛门救苦救难之正道。大师之意显然不反对为救国而杀敌,表现得不乏血性和斗志。 1940年11月,南安、晋江各县小学校长潘希逸(南社诗人)、林高怀等人就有关抗战时教师生计艰辛,可否改业一事请教时居南安灵应寺的弘一大师。曾是师范教师的弘一大师坦诚以对:“小学教育为栽培人才基础,关系国家民族,至重且大。小学教师目下虽太清苦,然人格实至高尚,未可轻易转途云……”(见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诸校长亲聆教诲,受益匪浅。
随着1941年仲秋的到来,弘一大师虽渐感晚年自身的衰朽,但仍坚持说法、讲经、普度众生。他在福林寺与杜安人医师交谈中,念及战时药物之匮乏,便把自己旧藏的十四种贵重西药赠予杜医师,嘱咐要普施贫民,真正培植“关心民瘼”的慈爱之心。杜医师深受感动,多次表达了悬壶济世的心愿。同年底,弘一大师因挂虑“开元寺因太平洋战事,经济来源告绝……道粮奇缺。”毅然将珍藏多年的美国真白金水晶眼镜一架“送开元寺常住变卖为斋粮”(见释广义《弘一大师之盛德》)。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慈悲情怀和无我境界。
1942年春,时在抗战大后方重庆的郭沫若正为历史剧《屈原》的上演紧张忙碌着,竟不忘致函向弘一大师请求墨宝。弘一大师录唐寒山大士诗书赠郭沫若:“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弘一大师借此表露自己“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傲骨和心迹,这与其在抗战初期倡导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及“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人生理念和艺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弘一大师“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朱光潜语)。可见他的人生轨迹与国家存亡、社会变革、民族兴衰、人民苦乐紧密相连。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伸张民族大义,坚持爱国至上,入世济世,慈悲坚韧,极力倡导佛教徒抗日护国,爱国赤诚昭然可见。他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座右铭,临终绝笔“悲欣交集”所蕴含的深意,流露出对芸芸众生的真切悲悯,及对祖国难以割舍的忧思和眷恋。其崇高的爱国精神犹如亭亭秋菊,劲节高标,绽放光华,流芳千古!
(作者系黎明职业大学教授、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执行编纂修订《弘一大师全集》。)
责任编辑:黄冬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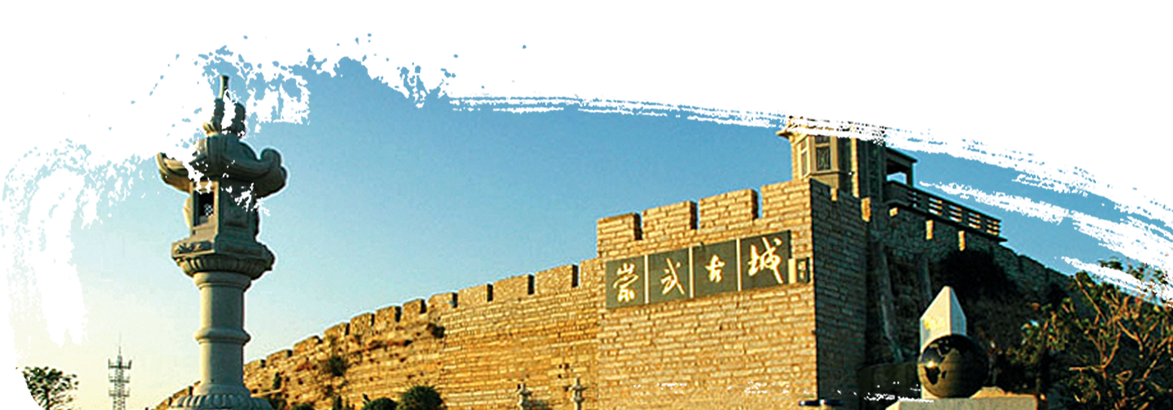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