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钩
发布日期:[2016-08-16] 阅读人:1637 字号:
一
1997年8月,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香港文学史》,这部洋洋六十万言的巨著在香港回归之年出版,不失献礼之义,也是对香港回归的一个最好的纪念。“香港文学是近代以来随着香港的开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在这特定区域、特定时间里,不断与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学思潮交会、冲撞、融摄,经历了与内地文学的互相延伸到独立品格的追寻,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现代化都市文化特征的中国文学的分支。”(《香港文学史》总论)。当我展读《香港文学史》时,我欣喜地发现有四位晋江籍的作家得到突出的介绍和高度的评价。他们是:司马文森、董桥、颜纯钩和施叔青。这四位作家,我只认识颜纯钩,并引以为朋友,因此,当我获悉晋江市政协意欲编印《晋江人在香港》一书时,便不揣冒昧地斗胆试笔,介绍颜纯钩君,以飨读者。
颜纯钩,笔名慕翼、斯人等。晋江安海人,幼年曾居港,后回国升学,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七十年代中期,一度在福州铁路局水电工务段当工人。1978年赴港定居,当过报馆校对、编辑,后任职天地图书公司编辑主任。1996年举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7年春,只身返居香港,并任天地图书公司副总编辑。
我和颜纯钩的相识相知,缘于与乃兄颜纯钧教授的相识相知,而颜氏昆仲则是孪生兄弟,无论是长相、才气和人品,都极其相似。所以,当我与颜纯钧成为好朋友以后,我对他这个孪生弟弟可以说早就熟悉了。
1948年6月23日,颜氏兄弟出生于安海一个华侨之家,其父抗战胜利后回国,在养正中学教英文。据说,这对双胞胎出生时,因是三代单传,全家上下额手称庆,在家门口搭起戏台,连演三天高甲。而为孩子命名,却把养中的这位英文教师难住了。孩子他妈只好先依序编号,大的叫阿一,小的叫阿二。孩子满月后,颜先生终于给孩子取了个好名字:阿一叫纯钧,阿二叫纯钩。取“钧钩致远”之意,而“纯钩”则是剑名。吴越春秋,越王允常命冶子铸造名剑,一曰纯钩,二曰湛庐,三曰豪曹,四曰鱼肠,五日巨阙。纯钩乃名剑之首。日后颜氏昆仲果然都很有出息,一个当了大学教授,一个是香港著名作家。
二
我于1986年和1992年两度赴港,都与纯钩有过几次茶叙,并作过一番长谈。在我们相处短暂的日子里,颜纯钩和我说得最多的不是文学,是文学以外的人生、社会,而我听得最真切的则是当年他抛妻别子只身来到香港的那段生活,那“曾经苦过,而且没有怨言”的值得回味的日子。那时他在《晶报》当校对,月薪只五、六百元,想买一本书、看一场电影都要惦量惦量,常常要在书店或电影院门前徘徊良久。他天天校对别人的文章,闻到报纸的油墨香味,他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几次拿起笔来试图写小说,可是屡屡被退稿。那时他无法认同自己,不能适应香港的社会。他感到痛苦、孤独、彷徨,夜里常在海边踽踽独行,直至深夜。那时他写给妻子的信比谈恋爱时的情书还要长,似乎只有这样夤夜孤灯的长谈,他的苦闷才得以渲泄,浓浓的乡愁才能够得到些许的慰藉。
但是,在困顿窘迫的境遇中,有一点他始终是清醒的,那就是绝不为物欲所诱惑,宁可找收入少的工作,也要满足精神生活。所以他才安于当报馆的一名小校对而不想跳槽。因为当校对有很多时间读书。在人欲横流的香港,他这种苦其心志的选择,实在令人钦佩。说起读书,颜纯钩还真有点轶闻趣事:“文革”期间,他姑妈在闽侯师专教书,有一段他躲到姑妈家去,他的卧室对面是学校早就封闭的书库。知识的饥渴使他产生“偷书”的非份之想,他终因书瘾难熬而撬窗入室,抱回一堆书,关起门来大嚼一通。一批书看完了,放回去再“借”一批出来,直到要离开了才全部归还。就这样,在焚书的动乱年头,他几乎读遍了“封资修”的古今中外名著,方知“书中有丰富的人生,而人生就是一本丰富的书”。到了香港,他才发现这里的书很多,香港并非像传闻所说的是“文化沙漠”。在《晶报》的那一阵子他经常跑书店、图书馆。“像一个一辈子没有尝过腥荤的人一样,把很多书当作山珍海味囫囵吞枣地吞下去。”他读马克思,读萨特,读弗洛伊德,读荣格,读乔伊斯、福克纳,当然,也看张爱玲、陈映真。如此潜心苦读,上下求索,一年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并非小说,而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政论,洋洋万余言,一泻江河。这篇政论发表以后,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香港《文汇报》主编读了他的政论,大加赞赏,遂聘他到《文汇报》任副刊编辑。这是颜纯钩在香港碰到的第一个伯乐,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不久,他又应天地图书公司之邀,兼任“天地”编辑,上午在“天地”上班,下午去报社。天地图书公司在香港是与三联书店齐名的大书店。那时,偌大一个天地图书公司就他一个编辑;而在《文汇报》,他同时要管三个版面,累是累了点,但是工作有兴趣,生活安定,“夫复何求?”是的,他感到很满足了。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写作,他只能挤出业余时间埋头笔耕,同时给二、三家报纸写专栏。
三
颜纯钩的小说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初,他的第一篇小说《迷茫》发表以后就引起文坛注意。当时他很佩服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胆识和笔力,读他的《山路》,直读得“老泪纵横”,不由联想起自己也曾经走过很长的山路,便也写了一篇同题小说《山路》。这篇小说写一个女知青的际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山路》荣获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这是他的第一篇获奖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久,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红绿灯》。《红绿灯》收入11个短篇,写的是小人物的悲剧,是大城市的哀歌;评论界视之为“创伤小说”,而颜纯钩的才气已经显现出来,一时间,颜纯钩俨然成为香港文坛的一颗新星,为人们所瞩目。
颜纯钩就这样走进了香港“绿印”作家的行列。所谓绿印作家,系指文革前后和八十年代陆续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作家,因他们在尚未取得永久居住权之前所持身份证上盖的是绿印而得名。这批作家人数颇多,单是闽籍作家就有三十多人。绿印作家是当今香港文坛的一支劲旅。而作为绿印作家的佼佼者,颜纯钩受聘于《文汇报》和天地图书公司,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颜纯钩的精神世界,与其说他拥有一张大报和一家大书店,倒不如说他拥有一个敞亮的心灵之窗。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流光溢彩的大千世界,是香港所特有的社会风情。但他更为关注的却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相互观照。他的文学创作大多围绕这样一个核心拓展他的画卷。他沉重地告诉我,他那些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充满沉痛的忏悔和清醒的追思,他似乎都不可能回避“悔恨”这个心理包袱。倒不是他做了什么坏事,光是虚掷十年光阴就够让人悔恨的。他初期的作品几乎都离不开文革这个背景,因为他对香港的生活还不熟悉,他只能去写那一场他亲身经历过的大动乱,去咀嚼一己的伤痛和悲苦。因此,他的创作一度停滞不前,没有什么突破,尽管笔耕不辍。
当他的创作面临困惑的时候,在评论界声名鹊起的乃兄颜纯钧,及时地向他指出他的小说囿于一时一事的局限性,提醒他务必扩大视野,方能追上时代的步伐。一席话使他顿然醒悟,于是他把视线落在大陆移民身上。他发现他们带着大陆的种种痕迹,突然走进香港这个社会,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而表现大陆移民的生活“为时下极受关注的题材”。虽然他写的依然是小人物的悲剧,但这种悲剧已经不仅仅是环境本身的问题,不仅环境要负一部分责任,而人的本性也要负责任,这样比揭露环境本身要深刻得多。中篇小说《背负人生》就是他经过反思后的一篇力作。他因此而获得1983年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小说创作奖冠军。《背负人生》写叔嫂发生暖昧关系,乃至非法同居,最后小叔子背负不起沉重的人生而自杀。其后的《天谴》也是一部悲剧: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姐弟俩相依为命,同住一室以至乱伦,从小就有恋姐情结的弟弟终以自杀了结他年轻的生命。恶劣的环境诱发出人性恶,终于酿成人间悲剧。《桔黄色毛巾被》描写一个画家无辜受到房东的忌恨和侮辱,他愤而与同情他、敬重他的房东太太同床共枕地做了一次爱,借以渲泄和报复,在酸涩的苦味中带着几分恶作剧的微笑。不难看出,颜纯钩的小说主题,大多写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存欲望。他笔下的人物由于外界的逼迫和内心的压抑太强烈,所以往往产生变态,作出一些有忤常情常理的行为,诸如乱伦、婚外恋、自杀,通过这种异常的事件来表现人物精神上受到的摧残压迫。读来别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却又扣人心弦,令人低徊。诚如著名评论家孙绍振教授所说,颜纯钩笔下的情欲主题,是情欲,但又超越于情欲,不是爱情,但又牵肠挂肚。
在《红绿灯》问世七年后,1991年,颜纯钩才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天谴》。这部集子收入14个中短篇。不知何故,那篇获奖小说《背负人生》竟然没有收进这个集子里。直至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香港新锐作家丛书,出版颜纯钩的小说集《生死澄明》,他才将《背负人生》收进去。同年,他在香港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自得集》,在大陆出版另一本散文集《母荫》。而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也向他组一本散文集。他写在《自得集》仅有一百四十字的序言中说:“小说写的是别人的故事,散文写的是自己的心迹。故人往事,历久仍新,家国忧患,点滴在心。一个普通中国人如此经历过生命中一段不平静的岁月,并以他的文字与读者分享。……所有欢心与悲情,悔恨与期望,都只是自得,因名之为《自得集》。”集子中第一辑的诸多篇什写的是往事与故人,令人魂牵梦萦的乡愁母题,“字里行间的喟叹与无奈,伤痛与撑持依稀可感,因此所包容的人生韵味就显得比较绵远。”也就是读了《自得集》,我才真正走近颜纯钩,更深地了解他。颜纯钩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散文,同时,他还是个电影剧作家。虽然他很少写电影剧本,但出手不凡。他第一次写的电影剧本《血雨》,就获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剧本征选优异奖,并出版单行本。后来,他又写了一个知青题材的电影剧本《竹坪旧事》,特地从香港给我寄来。剧本写一个女知青离奇命运的故事,揭示人性的摧残与良知的痛苦抉择的主题。我读罢,竟久久不能平静。但我明知这是不可能投拍的,因为触及一些“敏感”问题。我给他去信,为他的剧本未能推上去而扼腕叹息。他很快给我作复,表示谅解,并说日后有好故事再给我写电影剧本。他对朋友如此赤诚,确实把我感动了。颜纯钩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所以,他出书的数量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心结构之作。
四
颜纯钩一踏入香港文坛,就成为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积极参与组建香港作家联会并担任理事。作为作家和编辑,他时时关注海峡两岸的文学创作,尤其大陆文学创作的繁荣,更使他赞叹不已。他刻意向香港、台湾和海外介绍大陆作家的优秀小说。他主编《文汇报》副刊小说专版《世说》,特地开辟“内地女性小说选刊”专栏。这个栏目于1987年2月1日面世。首先连载福建作家陆昭环的力作《双镯》,并加了热情洋溢的按语。1992年,颜纯钩辞去《文汇报》的职务,任天地图书公司编辑主任,全身,心地致力于出版工作。他更加广泛地同大陆作家进行交流,而大量出版大陆作家的优秀作品则是天地图书公司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举措。
1996年,忽然听说颜纯钩意欲举家移民加拿大,乍一听到这一消息,不知怎的,我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怅怅然若有所失,想他这一走,倒真的成了去国的游子。……也许想到此去远隔重洋,遥遥无归期。待到一切手续办妥,他携太太专程返回大陆省亲,拜别故土。虽然,自从老祖母去世以后,旧居已是人去楼空,院子里那一株株翠绿的香蕉、番石榴和鲜艳的玫瑰丛,也早已了无踪影,他还是要回来看看。是的,祖厝屋檐下的燕子窝已是空有其窠,堂前的呢喃燕语竟成了梦中乡音,千古绝唱。
他向故乡投去深情的一瞥,便匆匆地告别了故乡,告别香港,飞往温哥华。那是1996年8月4日,临行之前,还记住把刚出版的《自得集》寄给我。我打开书,卷首开篇便是《故乡》一文。他写道:“有的人有第一故乡,第二故乡,我没有。故乡一生一世只能有一个,就像母亲一样,无可选择。”“等到在别的地方也吃尽苦头了,方觉得半生过下来,最可留恋、最快活的地方也还是自己的故乡。”我期待在故乡与他再相会,像往日那样,坐在他老家的院子里的番石榴树下,品茶、纳凉,伸手采摘枝头熟透了的番石榴。……
待到1997年1月,在他移居加拿大四个月之后,我终于接到他的信,他说他还要回香港来工作。读罢他的信,很使我高兴了一阵子。其实,即便他回到香港,而我在大陆,我们也还是难得见上一面。尽管如此,他的“回归”还是令人欣慰的。香港,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毕竟是祖国的领土,中华民族的骄傲。他劳作于斯,拼搏于斯,奉献于斯,他能不钟情于她!5月12日,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五十天,他终于从温哥华飞往香港,重返“天地”,并升任副总编辑,同时兼任《香港作家》杂志副总编辑。
1998年7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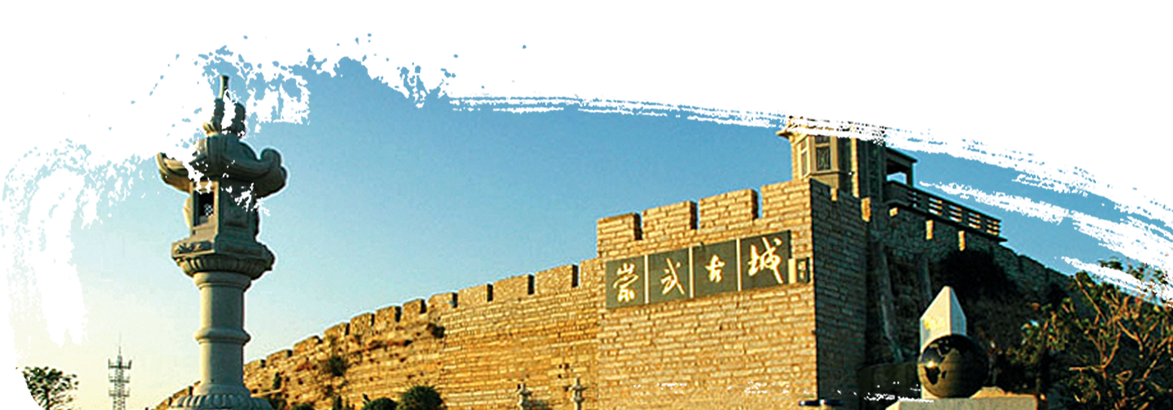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