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印度教寺址的调查研究
发布日期:[2016-08-16] 阅读人:1637 字号:
泉州印度教寺址遗留石刻七十四方,为我国现存唯一的印度教珍贵的文化遗产,其石刻雕刻艺术,既多且美,实为我国仅存不可多得的瑰宝。但因泉州地偏东南,迨古港衰落,游客零落,解放前后,未曾引人重视。一九五七年吴文良先生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始公开发表,引人注目。认为其宗教艺术冠绝诸教,实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印度教史迹。本文从调查入手,征引文献,以证实该教传入泉州的历史与地区的分布,最后推论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意义,作初步的探索,敬希读者指正。
一、泉州印度教寺址的调查
追忆五十余年前,我在泉州读书,常到南门校场附近考察,至今印象,历历在目。当时南校场为杀人场,备极凄清。旁有一小山,山下有小池。附近散布许多青石雕刻,颇为凌乱。池边砌以石刻,一如青石,叠成数行,整齐可观,这是我最初接触石刻的情况。
解放以后,郑振铎部长至厦大讲授中国小说版本问题,余亦往听。即告以泉州文物古迹十分丰富,并告以收藏最多的是吴文良先生。郑部长颇为重视,希望能到泉参观。后劝吴先生将其石刻献给国家,吴先生同意,于1954年9月1日造报福建省晋江专区,印成“交通史料石刻”一本,分类载明吴先生奉献石刻147方。该书印时遗漏四方(31-34)。在这147方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印度教石刻74方,其他为伊斯兰教50方,多墓碑、墓石,基督教等23方,亦为墓葬石刻。唯独印度教全为寺院石刻,未见墓石或其他,这是我在1954年所知石刻的最初情况。①
解放后我和吴先生因兴趣相同,常相率到泉州各地搜索类似的石刻。曾在开元寺(二支),天妃庙(二支),井亭巷(四支),讲武巷(二支)等地见到印度教青柱石刻计共十支。至今又三十年,除开元、天妃石刻尚存外,余皆不知下落。五六百年来的石刻,早已纷飞飘零,不知落在何方。所幸1958年泉州市成立“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多方保护泉州石刻,今后当不致再行散失。但泉州民家中如金刚巷某家庭中,尚有保存若干石刻,作为园庭布景之用,则知泉州印度教石刻散布的调查情况。
1950年林惠祥教授率领师生组织“泉州考古队”,归来写成调查报告,论及泉州印度教史迹。林教授曾西游印度,购来印度教崇拜物多件,正可使我们进行对比,故这批印度教石刻时常萦回脑中,必欲探其究竟。1964年林教授已归道山,我曾带同学来泉州实习,到“石笋”古迹,见其说明碑云:我国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文物,我认为石器时代我国未见如此石祖,不信其为我国文物。我调查过邻居,据云石笋石座在今石笋附近一公尺处,我请他们告我地址,并借我锄头一把,把掩埋石座的土层清开,始完全相信非原始社会遗物,盖石座刻有缠枝花纹甚明,和书上印有印度教石刻完全相符,乃知此必是印度教文物而非本土文物。这是我对印度教遗址最初考察的情况。
问题越搞越深入,兴味越来越浓,我已不能摆脱印度教文物对我的诱惑。忽又看到《海交史资料》中提到培英女中(今泉州幼师)校园中发现印度教祭坛一处。惜未调查而“文革”浩劫突起,吴文良先生又归道山。亲友零落,林吴二先生先后逝世,使我悲从中来,两先生已黄泉永隔,请教无门,不得已暗中摸索,写此论文,甚觉泉州考古界有飘零之感。后来看到苏联世界史,英国福斯特论文,他们附有吴先生所藏石刻照片,始知此类文物已引起国际的重视,遂更加留意于此。
1981年秋,余回泉州见过陈达生和吴幼雄两位同志,他们对此问题亦同兴趣,带我到幼师、南门实地考察,增长我一些知识。即使是片言只语,都是金石良言,很是可贵。本文的写成和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特此向陈、吴两同志敬致谢意。
二、泉州印度教寺址的分布
从上面调查的结果,可以知道泉州印度教的寺址不只一处,不只一座。其传入泉州,至少应该在公元八世纪的唐代,甚至可推测在唐代以前的六朝,决非夸大之词。古代文献中对外来宗教记载极少,对印度教史迹几等于零。但文物大量存在泉州地面,正说明印度教传入泉州历史的久远。这样悠久的文化交流,竟不得见于地志正史,实甚可惜。
幸而吴先生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中,录入《清源金氏族谱》附录泉州小说“丽史”一文的原文云:
元政衰,四方兵起,国令不行。其(蒲寿庚)婿西域人那兀纳作乱。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备极壮丽。②
这部族谱系我们三人(陈盛明、韩振华和我)1954年在泉州大寺后向金氏族人商借钞得的。该谱系明嘉靖年间所修,内附南安莱谙所作“丽史”一文,为证明金氏除那兀纳之功。除此以外,多杂以金南谷的行状,墓志。但其中有《丽史》及《重修清真寺碑》二文,为泉州历史的重要资料。此外本文有谱序四篇,宗支指掌一篇(1-9世),世系大略一篇(为总图表),传赞九篇,谱跋三篇,这是《金氏族谱》的大概情况,因和分布有关,附记于此③。关于番佛寺的历史,最初只见于这篇“历史小说”。当初金氏是回教徒,也不知此番佛寺是什么宗教的教寺,所以记载在他们回教族谱中。应该说回,印二教是敌对的,在他们族谱里所以记载“番佛寺”乃因他们不知道番佛寺是印度教寺。如果知道绝不能见之于回教族谱中。由于番佛寺记在回教族谱中,遂产生一个问题:“番佛寺”是回教寺呢?还是印度教寺呢?有了一些争论④。
我的看法仍然同意吴文良先生的意见。认为吴先生说:“元代泉州有婆罗门教寺一座,俗名番佛寺,位于今日的南门城附近一带,距今通淮街有一段路程。”南门一带,故称泉南,既有伊斯兰教寺,也有印度教寺和基督教寺,他们这些宗教,过去都是各据一方的。元朝对各教平等看待,为了要方便各教教徒中的商人,他们的寺院混杂在一起,完全是可能的。可是,《晋江县志》有番佛寺池的记载⑤,它的方位也很明确,而且池边散布了印度教石刻很多,可见番佛寺是指印度教寺无疑。如果在该处掘出回教寺的文物,问题就更复杂了。
现在,我们可以按顺序来介绍泉州历代所存的三个印度教寺址。
(一)西南新门外的石笋寺遗址
石笋最先记于《晋江县志》⑥。志称:“石笋在临漳门外山川坛西,石卓立二丈许,江在其下,故名‘笋江’。(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77)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明朝成化(1465-1487)郡守张嵒,补而续之。”宋代学者既不知石笋为何物,也不明其出自何国。以其形状如笋,遂名之曰石笋,附近的江流也称之为“笋江”(这里应考一下笋江地名)。实际上前文管部门也不甚了了,所以在说明石刻上只是说它是我国原始宗教的遗物,现在经过研究结果,才知道它是中印友好的文物。
为什么说:石笋一定是印度教的文物而不是中国的文物呢?其一、石笋形如男性生殖器,正是印度教徒所崇拜的神象。在公元前2500年到500年间形成的,正统的印度教徒认为《吠陀经》不是普通人制成的,而是经典本身对先知者的启示,是雅利安人最早的文献记录。在印度教徒中一直享有崇敬,认为是最高的宗教权威。甚至就在今天,印度教徒在出生、婚姻、死亡等所有的礼节上,还是按照古老的吠陀仪式来进行的⑦。《吠陀经》上所拜的神象湿婆,就是男性生殖器。石笋就是赤裸裸的生殖器。
其二、印度教徒是善于海上经商的民族,印度东西南三面临大海洋,人民早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通商,就在通商中把印度教传到缅甸、马来、印尼、占婆(越南南方)、柬埔寨等国,这些国家都有他们经营商业的据点⑧。印度和中国往来,先经东南亚各国,再由东南亚来到我国,自然印度教也会传入我国。如印尼的“婆罗浮屠”的建筑雕刻,就和泉州番佛寺石刻相似,其他各国的印度教石刻暂不多举。其神像各国基本上一样,就是信奉三个大神。
其三、中印文化交流早在秦汉以后就存在。汉朝我国使者就到印度的黄支国。六朝就有佛教徒来泉州翻译金刚经。印度教前身名“婆罗门教”,开始于4500年前,到公元前五世纪佛教起来改革婆罗门教,2500年前婆罗门教失势,佛教代兴⑨。后来,公元八九世纪佛教渐呈衰颓,不久佛教在印度本土枯死,传到中国、日本各国去,而婆罗门教进行改革,吸收佛教优点而变成“印度教”。所以印度教的再兴是唐朝以后的事,但唐以前有婆、佛共存的历史。泉州印度教可能是在唐以前传进来的。石笋便是早期婆罗门教的三大神之一。
其四、印度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图像,可参考英国人瓦尔《性的崇拜》一书。该书附有图版,和泉州石笋完全一样⑩。1964年厦大考古实习队到石笋,清理积土,发现基座完全是印度文饰的作风,印度考古学者曾在旁遮省、信德省发掘出男性生殖器崇拜像,为印度最原始的湿婆神像,和泉州石笋基本相同(11)。这种石笋是其初型,与林教授从印度买来的标本,一脉相承,但已有变化。这些都是考古的事实。泉州石笋在北宋已有记载,可知石笋系北宋以前物。
(二)西北子城西门外的印度教祭坛
唐子城西门外即今西街裴巷平水庙支巷,有泉州幼师(旧培英女中校址),在入门不远的校园中,有印度教祭坛遗址一处。也是青石石刻,但规模较小。遗物现藏泉州海交馆石刻室中。
察其遗物,确为宗教建筑,和壮丽的番佛寺比较,是具体而微的印度教作风,因其规模不大,又未进行发掘,故不为考古工作者所注目,先在1968年报道,1974年始为人所注意。就其地点观之,系在子城外,或为唐以前的印度教遗址。当时佛教已衰,印度教初兴,故其规模不大,仅具雏形。
泉州建城是在唐初,称为“子城”。外国人建筑常在城外,故我认为这个遗址是在唐子城建成以前。最迟不能晚于唐初。同安县亦有“婆罗门塔”,即为唐五代的遗物,也可以说是印度教初兴时(即中期)的遗物。唐朝以前泉州是设在南港,即今安海港,唐开元以后,泉州改在北港,即今后渚港。这个古迹可能是唐初或以前走南港时的古迹。
(三)泉州南门的泉南番佛寺。
泉州南门校场附近过去为外商集中的地方。各国外商麇聚于此,市面繁荣,即古所称“泉南”。印度商人即在此建立寺院,泉人以其风格与佛教不同,遂称之为“番佛寺”,以别于汉化的佛寺。《晋江县志》以其寺久废,没有记载,仅在水利项下记云:番佛寺池在城南隅。寥寥数字而已,亦不知番佛寺为何物。因此,有人以为即宋时的“宝林院”,由于资料缺乏,久成悬案。
查《宋会要辑稿》记有婆罗门教徒与佛教徒同行,前来中国,马可波罗和伊本巴都他都记载印度商人在泉经商,也没有提到这个寺院。马氏说:“印度船舶载来香料及其他贵重物品,咸莅此港。”伊氏说:“中国地区辽阔,穆斯林另有专城居住。在我到达刺桐城的那一天,正遇到那位带着礼品奉命到印度去的使者。”当他要回国时,“到达刺桐时,正巧有船要往印度。”他们提到印度人、印度船,却没提到印度寺。只有马可波罗提及“印度人之事物及举动,足供叙述之印度大事,至为奇异,确实非伪。”也许包括印度的寺院。(12)
我们为了这个番佛寺,曾经进行实地调查。据池边王家说,几家都被迁建。最后找到陶家,家长玉官现年74岁,住池边五十年。其子文质边讲边画,他说池作椭圆形,面积约六亩,东住池尾傅家,东北有小山坡,坡南有白石碑记,约二市尺,写三字直行为“番佛寺”,每字约十余公分,碑座作莲花形,对面有寺,住尼姑几人,寺下有青石柱二,为养牛太山拴牛之用。寺碑正确地点在粮食局仓库后,今电机厂内,(13)番佛寺已毁,仅存石像、石柱、龛状石刻等物。
以上三个遗址:一个在城西南,一个在西北,还有一个在泉南。他们分布的地点已经明了,为什么会分布在这三个地点,须待历史予以说明。
三、泉州印度教传入的历史
印度教为印度半岛各国人民所共奉的宗教,起源很早,四五千年前就已存在,后来衰落为佛教所代,一千二百多年前又复兴,直至今日信徒数亿,遍布东方。(14)至今对南亚、东南亚、东亚人民的思想生活,仍有巨大的影响。
印度教初名“吠陀教”,以其崇奉吠陀经典得名;又称“婆罗门教”,以教权操于婆罗门僧侣得名。后改称“印度教”,为印度半岛人民所崇奉的宗教。据张星烺先生研究,中印关系萌芽,远在先秦,秦汉以后,关系更切(15)。
我国汉代已有使者到印度黄支国。三国吴时,记有朱士行在“甘露五年(286)汉地沙门,欲得婆罗门书,惑民正典。”则三国时已有婆罗门的记载。两晋《法显传》亦云:“五天竺地,皆以婆罗门当贵姓。”南北朝时,由水陆传入中国。北朝《魏书》有“乌苌国婆罗门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之。”南朝《梁书》有扶南传云:“俗事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16)可知六朝时印度教已传入中国。
泉州港最早的交通史迹,始自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在泉州南安九日山翻经。当时佛、婆二教并存,故有印度教传入的可能。
“石笋”位于泉州西南,(17)“祭坛”位于西北,六朝闽南中心是在丰州,丰州地近西南、西北,当时海上交通可能先自泉州南港,即今安海港。安海水头曾发现西周古越人墓葬。(18)则印度人自安海北行,过安平桥达金鸡桥,可到南安的丰州,今泉州未建城时,子城系在丰州,印度人来泉共住在今泉州西南、西北,故有“石笋”与“祭坛”两个遗址。那时印度人的商业区、住宅区,应在今泉州城的西南、西北,与阿刺伯人居住东部、东南部有所不同。不同宗教有不同仪式,划地而处,互不干扰,极有可能。在泉州西南、西北的印度人区中,有住宅、商店、寺院,极其自然。故我认为石笋东边的天地坛,应为古印度教寺所改建的,而祭坛附近亦必有寺院,以供印度人的礼拜。则这两个遗址应兴建在唐泉州城迁建以前,是极其可能的。
泉州港在唐代开元年间,迁治建城。从此,由小港变成大港,由全国性变成世界性,扶摇直上,历宋元而极盛,明代以后始衰。“番佛寺”何以不建在西南、西北,而建在泉南,这是由于商业中心的改变,印度商人必须与其他商人群居在泉南,为印人崇拜的方便,寺院改建在商业住宅附近,亦势在必然。番佛寺改建在城南乃商业中心南移的明证,故该寺建筑时间,必在泉南兴起以后,可断然也。
我们读了《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述及印度教传入广州的情况云:“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有婆罗门教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崑等舶,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19)这段记录说明唐朝开元天宝时,广州港对外贸易极盛。印度船、印度货、印度商人及印度寺,印度僧人的情形,备极清楚。则唐朝以后,泉广成为对外贸易的大港,印度教徒随着商业的发展,自广州传入泉州,必在唐朝以后。宋元时代泉南特盛。宋代《诸蕃志》云:大食巨商侨寓泉南。元庄弥郡罗城外壕记,称“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20)则“泉南”一名,流传于宋元时代,《金氏族谱》称番佛寺建于元末,毁于至正,前后不过十年。此寺石刻,备极壮丽,规模宏大,雕刻极精,远非十年所能完成;而且内乱频仍,战火纷飞,亦难于施工,故云番佛寺建于那兀纳,实足令人置疑。陈达生同志的大作中,有“那兀纳与番佛寺”一节,(21)称那兀纳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杀阿迷里丁,接管亦思巴奚部队,至二十六年(1366)为陈友定擒杀,历时四年零四个月。史称:西域那兀纳,回寇那兀纳,则那兀纳为西域回教徒,似无可疑。印度亦有回教徒,但回教徒不可能建印度教寺,实有矛盾。
这确是一个困难问题。陈同志把那兀纳解析为阿刺伯人,番佛寺即回教寺,撒金豆为回人风俗。但番佛寺池边的石刻,完全是印度教石刻;把番佛寺说成为回教寺,寺内并无“番佛”可言。故我仍认为番佛寺为印度教寺为宜。
至于那兀纳是否印度人,他在战争中是否会建“番佛寺”,亦有怀疑的可能。印度教徒何以能与回教徒联合作战,也难理解。我认为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形势迫使他们联合对敌,亦有可能。蒲寿庚、郑和等政治家,既可为回教信徒,亦可为佛教信徒,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回、佛既可兼信,回、印何独不然。为求外族人民的团结,以共同对付元朝,他们结成联盟,并非绝不可能,即宗教服务于政治。此问题的解决,有待他日史料较多时继续探讨,故陈同志仍云“此番佛寺或即印度教之俗称”,亦未敢决断认为“番佛寺”为回教寺。
但我相信泉州南门的清净寺址,为回教寺重地之一,他日必有解决之一日。印度人能否作为亦思巴奚军的领袖;回教内部是否因教派不同而分裂为二?所有这些问题,均有待将来进一步的探讨。
四、泉州印度教史迹的意义
泉州有三个印度教史迹,已如上述。泉州港盛时,有印度商人居此,文献已可征引,这里尚有人提出,男性生殖器崇拜是否为印度人所特有?印度人的原始宗教为多神的偶像崇拜,她与回耶独尊一神,截然不同。即佛、印同为偶像教徒,所拜的偶像亦绝异其趋,佛教拜的是人像,如释迦、观音等,印教拜的是神像,特别是最大的湿婆神(SIVA),湿婆神形状不一,有用神像,有用“林加”(LINGA),印度人除信湿婆外,还信有梵天、比湿拏三位一体的神像。印度人认为湿婆为“宇宙威力之神”,男性器官为生殖的主动者,他可使生命永远存在,而生生不已,故称这种思想为“生生主义”。女性受胎为生殖的功能,若一女子不能受胎,为终生的缺憾,必求助于湿婆这个神明,农民欲得丰收,牧民要得多畜,商人要得多财,工人要得多器,均须崇拜林加,则崇拜林加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其生命力极强,一直延续至今。
教寺的建筑,须赖商人,那兀纳总番舶,为泉巨商,故能造此堂皇富丽的“番佛寺”。其遗物中有立姿雕象,吴先生定为比湿拏神像(115图)。(22)此外还有石柱、石龛,亦刻有变形的生殖器称为“磨盘”,为男女性结合的象征,(23)与石笋全然不同。所有这些石刻都带有极其浓厚的印度作风。而石刻中,亦留有印度故事与中国花草,为中印文化的结合。
印度半岛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都有印度教的崇拜。这种宗教对印度社会仍有深刻的影响,从思想到生活,都有其烙印。印度贱民仍如美国的黑奴,遭遇凄惨,但愿有一天贱民与寡妇都得解放,享受幸福的人生。
中印、中南关系悠久,这种传统的历史友谊,已为泉州历史文物所证实,这三座印度教文物古迹,实与清净寺相同为泉州交通史迹。印度教寺已被毁,希望吾政府对这全国唯一的印度教寺,予以恢复,供人参观,以表示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中南人民友谊长青。
庄为玑同志: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庄为玑:《泉州文物调查初集》1954年复写本。又见吴文良:《泉州对外交通石刻集》序言。
②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59。科学出版社。
③《清源金氏族谱》手抄本,厦大历史系资料室存。
④陈达生:《关于元末泉州伊斯兰教研究的几个问题》(宁夏回教史讨论会油印稿)。
⑤清乾隆本《晋江县志》卷二规制志水利。
⑥清乾隆本《晋江县志》卷十五古迹条。
⑦恩·克·辛哈:《印度通史》第一册,页61-62商务本。
⑧同上,第十一章印度的交通条,页331-348。
⑨同上,第五章第二节佛教,页90-97。
⑩英人瓦尔的《性与性的崇拜》O·A·WALL“SEX AND SEX WORSHIP”附图版。
(11)常任侠:《印度和东南亚美术发展史》页2。1980,上海美术社。
(12)马可波罗及伊本巴都他的游记。
(13)见1980年5月15日的调查记录(草稿)。
(14)朱天顺:《原始宗教》,页50-53。
(1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中华本。
(16)见《法显传》、《魏书》(乌苌传)、《梁书》(扶南传),及注③。
(17)张东民:《性的崇拜》1927年,北新书局本。
(18)庄锦清:《南安大盈西周史迹简报》,《考古》1975.10。
(19)《唐大和尚东征传》及《通典》婆罗门条。
(20)宋《诸蕃志》及清《晋江县志》。
(21)陈达生:《关于元末泉州伊斯兰教研究的几个问题》(宁夏回教史讨论会油印稿)。
(22)印度库玛氏:《泉州印度式雕刻》,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
(23)《厦大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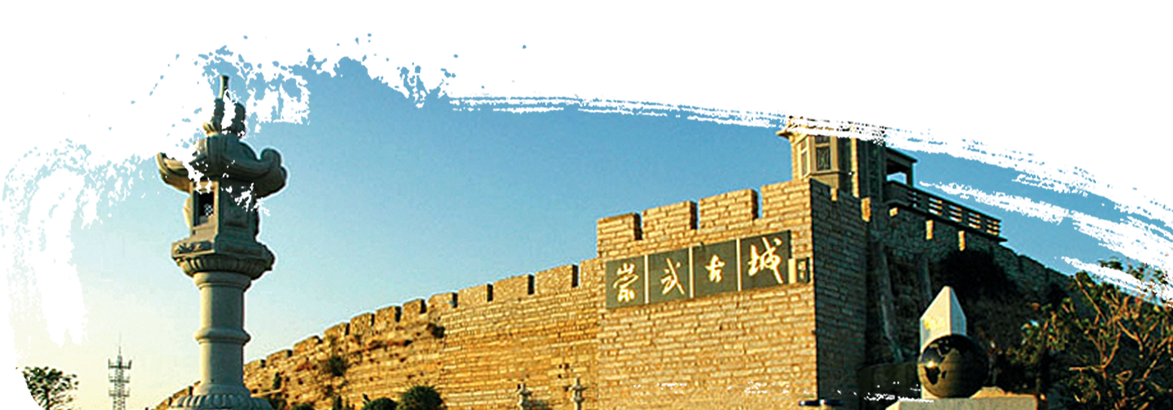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