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宗教生活
发布日期:[2016-08-16] 阅读人:1637 字号:
一、担任教会工作前的经历
(一)童年时代的宗教影响
我生在晋江一个农村的贫苦农家,六岁丧母,九岁随父亲到安海谋生。一九一二年,父亲得在教会当顾堂工,我也进入教会附属的铸英小学念书。眼看英国传教士来来往往,他们吃好,穿好,随带行李又一箱箱地,还有很多工友跟从。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触动了我,就这样引起我崇英、亲英的思想。
我在小学念书时,因聪颖、理解力强、反应快,安海牧师黄日增为我引进给常常经安海到泉州的英人安礼逊,于是我在一九一五年春天免费到泉州英国长老公会创办的养正小学(培元小学的前身)念书。
当时,有位英人教师温德喜教我英语,对我的勤学和认真颇有好感,很关心我的学业。温德喜常主持朝会,有一次讲到“人是猿变的”,触动了经义,因此来泉只一任就回国。另一位英国教师骆约翰,好体育,常与学生接近,也因不严肃而回国不来。这两位英国教师对我在宗教启蒙时代有深刻的影响。这是我以后宗教生活反反复复,欲就欲离的主要根源。
(二)中学时代的宗教生活
我是从亲英思想而接受宗教的,这主要在培元中学念书的时代。学校每次朝会,安礼逊都从阐明校训带入宗教的传播,他经常提起“真理,自由,服务”的校训,而三番五复地说明真理是耶稣基督,自由是强盛,应当信基督才能强盛,为此而服务,才有目标。他也常提到“爱”,讲上帝爱世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也常提到“祖家”(指英国)的信徒怎样热心事主。这样提法,使我分不清界限,与“天堂是我的祖家”相混起来,在信仰的目标上有些混乱,但接受宗教的思想,还是加深一层。
当我念到中学毕业班的时候,安礼逊问我毕业后要做什么工作,我回答他,要做传道。我这样回答,主要是我的父亲的愿望,父亲因信仰较深,早把我私自献出要作圣工了。安礼逊听后很高兴,就主动地为我向英国长老公会申请资助,并与南京金陵神学院联系,这是我被造就以后担任传道牧师的基础。
(三)神学院时代的宗教思想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学习,当时所有费用都是由英国长老公会付给的,用过多少,我不知道,只是在领取一部分交膳费的款项时,要亲自签字领出。这个约字中唯一的条件,就是毕业后必须回到闽南基督教会中做传道。看过这样的条件,我有些震动。由于我从小学而中学,现在到大学,都是得到英国长老公会的帮助,头脑中还是存在亲英思想,明知他们培养我,主要是要我作宣传宗教工作的,但这个思想残余还是在我脑中存在着。
当我在神学院念书第二年时,便产生了停学的思想,认为我应当做教师好些,并向当时培元中学校长许锡安提过,而他在回信中劝我应当念到毕业,毕业后可回到这里来当中学教师。因此,我就耐着性子,一直勉强学到毕业。这是我当时宗教思想的反映,也说明,我在某种程度是不安心的。
二、工作的开端
(一)脱离传道工作的经过
我从神学院毕业后,应当要参加教会工作的。这时,一手提携我的安礼逊,已往新加坡当牧师,不在泉州。代理英国公会工作的是罗励仁,他一听说我回来,就请我到他家里座谈。谈话中,我坚决表示要到中学教书,他听后,很严肃地对我提出说,你是英国长老公会资助的,应该当传道。争执不下,气氛很僵。当时我年少气盛,我想,他们怎能用钱来支配我呢?便悻悻地不辞而离开。罗励仁也无可奈何,但他想,在教会学校中必定没有人敢聘请我。可是过了不久,泉州南街礼拜堂牧师高萃芳,这个与英国公会素怀意见的,一闻知我的情况,就聘我担任南街堂会办的华英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只约定在他外出赴会时,替他主持礼拜日的讲道而已。我这个拒不做传道的事,引起以后英国长老公会不再资助人到南京神学院去学习了。我的父亲也因此对我不满。
以后,东石龙江小学聘我为校长,安海养正中学及泉州培元中学也先后聘我为教师。我就这样一直担任教师工作到一九三八年年底。
(二)我在传道工作中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培元中学迁往南安九都,我一家大小六口人,也跟着学校迁移。在九都住宿很挤,加上父亲因我不当传道而不给任何帮忙,当时生活很艰难,幼儿又常闹病。当学校又拟再迁入内地时,我便萌起当传道的思想来。刚好当时在南街礼拜堂为长执的同乡许子杰闻知我的想法,就向长执会推荐,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应南街礼拜堂之聘,携眷回到泉州。罗励仁知道后,认为我已履约遂他们之愿而欢喜。我的父亲也以我能遵他的志向而有所垂顾。南街教会会友认为教会有人可司讲道而放心。各方面都热情支持。这时我在思想、生活颠波中得到安定而定下来了。
(三)在南街礼拜堂担任传道牧师工作中
我已怀着回归教会工作的信念,就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基督信徒而工作。因为社会上对我必定会另眼相看,信徒也必察看我的行动,所以自己的要求:应当是品德要高尚,躬行要廉谨,讲道与行为不能相悖,应常以此自省。凡是有关宣传基督教的工作,都尽力以赴,也不问提倡的人的目的如何而为罗励仁的国语崇拜会讲道。以后又参加监狱布道,记得有一次,在何大年先生家中遇到被控滥捕杀人的前安溪县长吕德超,他是因为监狱布道托罗励仁说情,保外就医而出狱的。我也时常为惠世医院兰大辟在手术前作祷告,并几次被他聘请为惠世医院青年团契会讲道。
抗战胜利后,海疆学校由仙游搬回泉州,英人安慕理适在这时也来到泉州。安慕理对我提出他想要帮助海疆一些青年学习英语,拟在南街礼拜堂组织一个英文查经班,每周星期二下午四时半举行。那时,我认为这是对青年布道的好机会,也乐于协助,以后安慕理也因这样而被海疆延聘为英语教师。
抗战期间,由罗励仁组织的“守望团”,作为泉州市内及城郊教会的牧师、传道的进修聚会,提高教会工作人员的灵性团契生活,我们这些牧师、传道都参加,当时认为这是提高自己灵性修养的聚会。
这些工作,虽然是教会工作的分外事,但那时都认为是一个基督教会担任职务的人所应当做的,也不问其性质如何。这是我以后头脑较清醒时,才能辨明它的是非。
南街礼拜堂的会友众多,意见纷纭,处理会务,本就煞费苦心。在抗日战争时,布道奋兴家宋尚节博士、林佩轩等来南街堂会讲道后,造成了会友与牧师、长执间的隔阂。本来教会奋兴会的目的是要加强会友的宗教信心及提高灵性修养的,但是这次却引起会友思想上的混乱。于是会务难于推行,迫使高萃芳牧师辞职,就任闽南神学院教师去了。当时有位得英国女宣道会津贴的女会友邱碟来协助开展女会友宣传工作,也因对奋兴会的看法不一致,思想上有抵触而矛盾重重。以后虽聘请了王洁斋、陈淑虔等来协助教会事务,也因工作上、信仰上有些混乱而难于协调。连比较老练的牧师陈思明也数次推却,没有应聘。我就是在这种局面下,接受南街堂会的聘任,难免产生怕难的思想。但想到为教会工作,应当要克服困难,团结同工及信徒。在信仰一致之下,教会工作也渐渐恢复了常态。
一九四○年,培元中学在泉州开班时,我再到培元兼课,以微薄的收入,过着淡薄的生活。后与学校联系,拟专职作教师。消息一传出,南街礼拜堂的会友,纷纷挽留,才未成为事实。
我一面对教育事业比较关心,特别对幼儿教育更注意。在我任南街堂会牧师时,对充实华英幼稚园的经费颇有决心,主张把教会的十间店屋。拨给幼稚园作基金,因而遭受个别较有资财的长老的反对。解放后,华英幼稚园归政府接办,店屋也被接收,引起了他更大的愤怒,埋怨我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以后的事。
一九四六年夏,香港伯特利神学院的教师曾牧师乘来泉探望他的母亲之便,鼓励我到香港担任牧师。以后,香港教会负责人黄诗田先生即来函约定,并在香港为我任职牧师准备好一切;一九四八年,印尼泗水林文彬先生连续来了几封信要我到那里担任牧师之职,他连入境手续都为我办妥。这两次往海外担任牧师之职,也都因泉州南街礼拜堂会友的热情挽留而打消了。
这是我费尽苦心在混混乱乱的思想中,一直担任南街礼拜堂牧师之职,直到解放。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提出“爱国爱教”的明确目标下,克服我这混乱的思想,而更有信心、更有方向地和会友一道为教会工作尽一点力量。
(一九八三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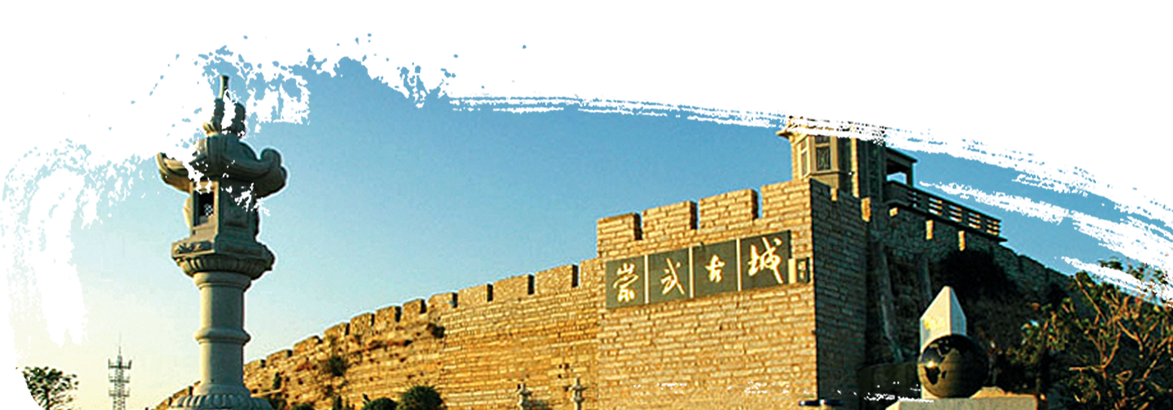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