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在泉州抓丁的罪行
发布日期:[2016-08-16] 阅读人:1637 字号: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军兴,当兵御侮、保卫国土为中华男儿之天职。时泉州驻军陆军第八十师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以保卫乡土的名义,组织晋江县基干队训练班,命令全县各保选送十八岁至卅岁的壮丁二名,随带步枪二枝参加训练。训练期限规定为三个月,结业后回到各联保组织自卫团队,协助驻军保卫乡土。哪知受训期满,钱东亮竟不顾信义,把受训的基干队员一律拨充陆军第八十师所缺的兵额,开赴省城,当兵入伍。当时参加基干队受训的人有不少是单丁独子的,按照兵役法的规定是可以免役的,但为了杀敌卫国,他们也勇于应征,惟对钱东亮的欺骗是不满的。这是抗战开始后晋江第一批入伍当兵的壮丁。这批壮丁都分别先后开赴前线效命沙场。有不少人战死了,也有不少人逃回来了。据逃回来的人说,先是他们也打日本鬼子,后来不打鬼子了,而打什么“真四亲”,所谓“真四亲”就是新四军。
随着征兵的开始,征兵的机构也相应设立了。晋江的征兵机构设立于1937年,首先名曰晋江社会军事训练总队,不久,即改名为晋江县抗敌自卫团,翌年又改为社会军事训练总队。1939年社会军事训练总队撤销,成立县国民兵团,县长兼任团长,另由省方派员任副团长,下设二股,专办徵募、组训工作。1942年,县国民兵团奉令改为县第五科,1943年又改为县国民兵团。抗战结束后,县国民兵团撤销,另设县军事科,由省方派员任科长,下设三股,办理徵募、组训、保卫等工作。乡镇则设兵役事务员及乡镇队副各一人,各保也设有保干事及保队副各一人,负责办理征召壮丁入伍。自从征兵机构成立后,相继还设立一新兵招待所,内设正副主任各一人负责管理入伍新兵,以便分批送交永春团管区派下来的接兵部队。该所内部黑幕重重,被抽召的壮丁一人新兵招待所就像进入监狱一样,不但完全失去自由,而且受尽敲诈剥削。所里公开设赌,美其名曰供新兵娱乐消遣,而其实则为管理人员大发横财的手段,他们除了抽头获利之外,主要的是定下圈套,千方百计从赌博中对新兵进行榨取掠夺。至于克扣军粮以肥私,贩卖物品以渔利,那更是家常便饭,不用说了。新兵们受此重重敲诈剥削,至出发前大多已囊空如洗了。
当时征兵的法规,定有“三平原则”:①家有三个壮丁的抽两个,有两个的抽一个;②单丁独子不抽;③家庭专赖维持生活者不抽。此外在职的公务人员、教职员、交通运输的技术人员以及在学的学生等均可免役或缓役。虽然有此规定,但弊端百出,该抽的不抽,不该抽的则抽,于是许多人弄得家破人亡,惟办理兵役的人员,则从中大发其财。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强敌压境、国家危急之时,凡是爱国男儿均义愤填胸,决心效命疆场。但由于当时蒋介石反动集团纯粹借抗日之名而实行反共反人民之实,于是即把自己嫡系的军队留在后方,企图保存其反革命的力量,而把一些杂牌的军队及新抽召的壮丁赶到前线去作炮灰。因此,广大的人民群众都不愿意为蒋介石去送死,而想尽方法来逃避兵役。这时候一些机关团体、学校则“生财有道”,大开方便之门,作为中签壮丁和适龄壮丁的避难所。例如晋江县商会蔡鼎常组织的消防大队,招收了吴耀光、朱天佐、邓国纪、黄绳武、张金赏等很多避役的壮丁去当该队的队长或队员。又例如泉州日报、福建日报、晋江县卫生院等也都成为当时的避役机关,本市合美布店的小老板李鹏翔、某照相馆的小老板庄百龄,都做了报社的挂名记者。许源兴百货店的许家齐则做了卫生院的防疫员,后来又居然升为法石镇卫生所的主任。而晋江县的警察局也组织义务警察队来吸收避役壮丁。所有的壮丁逃到各机关团体去避役时都要花了一笔运动费,向该机关的主管买好,例如涂山街头庄诗宗以伪币一千元向警察局警官运动,才当了义警,得到了缓役。一些中学学校在这时期也利用机会大量收生。
当时的一些联保主任,利用征兵与暴吏互相包庇、互相勾结,滥捕壮丁,有钱有势的,家有五丁以上,可以不服兵役,而无钱的贫苦人家,虽是单丁独子也被拘送入伍。在这种“有钱则生,无钱则死”的苛政下,穷苦人过的是“四处逃亡,妻离子散”的惨痛日子,因此民怨沸腾,仇恨日深,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歌谣:“不怕日本兵,只怕陈文英(云梯镇联保主任);不怕日本鬼,只怕何光伟(象峰镇联保主任);不怕日本船,只怕何健魂(明伦镇联保主任)”。这种歌谣充分反映出当时广大群众对暴政深恶痛绝的反抗呼声。
为了逃避兵役,还有不少人在兵役期到来之前即无病装病,例如本市后城张瑞坤的儿子张端生即打通了卫生院的关系,装病抬进卫生院去避役。又如鲤东保居民张维秉亦为避役计,竟将右手食指用菜刀斩断。至于拆户分爨、改名换姓、离乡背井、流落异地以求幸免的人,则难以胜数了。
“三平原则”实行了不久,由于弊端百出,兵源日竭,反动政府即把所谓“三平原则”取消,而代之以摊派的办法,即以各保的壮丁多少为比例来分配征召的数额,这种办法改变后,就不用抽签了,可雇人顶替,反动统治者美其名曰“有钱出钱,有人出入”。实质上,这种新法实行后,弊端更多了,穷人更该死了。当时的情况是:有势力的人不必出人也不必出钱;有钱的人出了一些钱就可以了事;而没有钱的人则既要出人又要出钱,弄得家破人亡,惨不忍睹。这样一来,所有办理兵役的人员就可以更凶恶地挥舞他们的一双黑手,一手抓人,一手抓钱,而一切与办理兵役有关的部门也可以随心所欲,贪污舞弊大发横财。
随着兵役征召的开始,就有了检查新兵体格的医官,这是个“肥职”,贪婪这块肥肉的人很多,大家争相抢夺,结果是落在与县政府和卫生院大事勾结的中统分子陈振辰及其妹夫张天赐的手里(陈是南生医院的医生,张是该院的配药员)。所有的新兵都要经过他们检查合格才得算数。因此,各保长在送交壮丁给新兵招待所之时,为了送去的壮丁能通过体格检查之关,都要向检查体格的医官巴结,赠送财物,进行贿赂,要不,就要受到医官的刁难。另一方面,被征召的壮丁的家属,为了自己的子弟免去送死,有些人就千方百计弄到一些钱,央三托四向医官买好,期望能取得一张不合格的证明,从检查体格这一关逃出来。就是由于检查体格的医官有些生财之道,所以后来永春团管区派下来的接兵部队也自己带来了一、二个医官,对新兵的体格进行复查,这样,矛盾就产生了。这个矛盾各保长还是请财神爷来解决,虽然要受了一些麻烦,但倒霉的反正是壮丁的家属。
当时,反动政府对接兵部队征补兵额,有个可以打九折计算的规定,即一百名之中可以扣除十名,作为途中死亡或逃跑的数额抵帐。这一规定就给接兵部队的长官带来了发财的机会了,即把折扣的名额卖出给各保,具体的做法是接兵部队出了收条给保长,写明收到某保壮丁多少名,保长即把收条送给联保转呈国民兵团抵额。国民兵团的负责人知道了这内幕,就不给抵额。各保长也知道国民兵团可能会不卖帐,所以事先都做好了行贿的准备。保长向接兵部队买了一名壮丁的条子,一般需要赤金一两,但保长总是向家有壮丁的人多派一些的,这些多出来的赤金,即被保长与其他办理兵役的人员吞下一部分,其余的即留待送给国民兵团之用。由于利欲薰心,接兵部队往往超额卖出,不敷之数,则在回归永春的路上相机乱抓路人来抵额。所以接兵部队路过的地方,在田间干活的青壮年都要闻风奔逃,否则就要遭到灾殃。
接兵部队的长官必然要和地方上的黑暗势力相勾结。这班地方上的恶势力,每每接受其亲戚朋友的委托向接兵部队行贿,接兵部队对此是有求必应的,但为了掩盖人家的耳目,他们舞弊的方法是很多的:有的是在征补后行将出发的前夜,偷偷地于更深人静的时候把人放了出来;有的是把答应要放走的壮丁选充为接兵部队的文书,不给月薪,过了一段时间,准其告长假还籍;有的是派为部队中的勤务兵或传令兵,不久之后,让其开小差回家。
自从应征的壮丁可以雇人顶替之后,买卖壮丁的“牛贩”也就应时而生了(卖壮丁的人叫做“人牛”,中间者叫做“牛贩”),“牛贩”有大“牛贩”小“牛贩”之分。小“牛贩”几乎每保都有,他们都与保甲人员互相勾结。大“牛贩”则要有大势力做靠山,例如大“牛贩”金为霖,他的靠山就是当时新门街的恶霸王鼎铭(王的弟弟王粿也是大“牛贩”)。大“牛贩”是纯粹以贩卖壮丁为职业的,他家里经常都有一些不事正业或没有职业的人,平时“牛贩”借给他们一些钱用,他们欠了“牛贩”的钱,也就无形中被“牛贩”束缚住了,到后来只好做了“人牛”,让“牛贩”把他贩卖了。通常一个“人牛”可贩卖赤金二两,“牛贩”即可从中榨取二成至四成。此外,则另有一些流氓无赖专门受人雇替兵役为生的,例如本市义春人吴瑞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往往在入伍的时候带了一些金饰,入伍后即利用种种的机会向接兵部队的长官行贿,于是不久就得托故请长假回家了。这人又和泉州兵役机构的主办人有了勾结,回家后不久,又再改名换姓顶替入伍了,如是者数年。接兵部队一面放他回来,一面又派员来泉向该保的保长交涉,说是该保的某某壮丁逃跑,要保长负责抓去缴交。保长明白这是接兵部队又来敲诈了,就去向雇主的家属迫钱,于是雇主的家属又要花一些钱才能了事,而保长也乐得利用这个机会随手捞了一些。
在苦难的日子里,广大的人民群众遭受兵役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新兵在永春团管区编训后就得拨充给前线的其他部队,出发时必须经过德化、大田的高山峻岭,接兵部队深恐新兵发生哗变,遂以暴戾的手段,将每五个新兵编成一小组,用铅线紧绑其臂连成一串,使其互相牵制,不能单独行动,这样,跋涉山岭就苦上加苦。当时内地山县物资缺乏,如能运往出售,可获厚利,接兵长官为了发财,即令每个新兵背负食盐及沿海土特产廿斤,翻山越岭,远途跋涉。新兵们由于受尽辱待折磨,受尽饥寒交迫,又因水土不服,往往生病。本市东街土地巷人蔡金成,于1939年被征召入伍,路经德化,因患疟疾,寸步难行,接兵长官认为妨碍集体行动,即开枪把他击毙。击毙后即责成当地保长具结证明该壮丁犯有逃亡之罪,故被当场击毙。与此同时,还有本市郊区华洲人(姓名不详)也同样因病不能走动被击毙在路上了。像这样残酷的事情,真是旷古未闻的。当时的老百姓说:兵役就是“瘟疫”,办理兵役的人员所到的地方,使生灵涂炭,鸡犬不宁。县国民兵团每于前线告急、兵役紧张之时,就竭泽而派员下乡催征。所派的都是主管的心腹。这些催兵的人员一下乡,就张开两手,一手要兵,一手要钱。而乡镇及保甲长除了天天设筵欢宴,召妓陪酒、陪赌,刻意奉承外,就大张旗鼓抓起壮丁来,白天派,夜里抓,只要是壮丁,不管有病无病,不管是否单丁独子,不管是本乡人、外乡人或者是过路人都抓,抓来了以后再说。所以催兵的人员一下乡,村庄就路无行人,家无壮丁了,所有的壮丁都逃到山上去,藏匿在墓坑里。坐催的期限满了,催兵的人员要返县复命了,各保都要送红包(草鞋礼)给他,为他送行。催兵人员除乘机敲诈勒索外,还有持势压人、进行迫婚的。1942年晋江县兵役科长卢贵寿在永宁镇坐催兵役时,即和该镇镇长高武鹄串通,以强行征召一个侨属的独子为手段,迫其把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儿嫁给他。这个侨属在淫威压力之下,束手无策,只好从命,以保全其儿子的生命。卢贵寿敲诈壮丁的钱也是很辣手的,明伦镇侨属何应年,即被其敲诈伪币二千元及派克自来水笔一支。
至于办理兵役的基层人员如乡镇长、乡镇兵役事务员、保甲长等等,他们在兵役事务中为非作恶的事也是罄竹难书的。如西北镇镇长吴友根抓了西门外塔后村刘贤钩入伍,入伍后刘受尽折磨,患了重病,经告假回家,不久也病故。刘死后,吴友根又将其唯一的弟弟刘贤螺抓去,刘的家属无可奈何,只好卖了田地和一个小孩得了千余元向吴买好,始得把人赎回。
又如开元镇镇长林培昭,此人横蛮至极,硬要抓大寺后爱娘的长子颜德芳去当兵。爱娘虽有儿子三人,但次子和三子均年幼,家中生活全赖其长子负责维持,因此,爱娘即把其次子卖掉,得八百元交给林培昭,托其雇人顶替。越年林培昭又向爱娘要壮丁,爱娘被迫没有办法,又将其第三子卖了五百元给林,谁知过了不久,林又来要其长子充役,至此,其长子即离家逃命于漳州。爱娘一时刺激过甚,突然发疯,家中所有一切器物均被恶徒盗窃,房屋无人管理,日久破烂不堪。到解放后,其长子始由漳州回家,而林培昭也罪有应得为人民政府镇压了。又如明伦镇兵役事务员郭国桢,曾拘捕张炳去充兵役,张的家属急向亲友借来款项(值壹两多的黄金),托郭代为雇人顶替,谁知郭丧尽天良,把款吞没了,又把张送交给接兵部队充役而去。郭还明目张胆包庇壮丁,本市济东口恒裕银庄经理林钻甫及本市某金铺老板陈蒿山为了避役,每月每人都得交保镖费。又如本市后城人郭维经,由于避役一向逃亡在外。1940年他的父亲年老病故。出殡之日,郭维经欲回家尽人子之道,执绋送终,但恐被郭国桢抓去充役,即由保长经手廿元(相当二钱黄金)向郭国桢说情,而郭只答应保他在送终之日无事而已,隔天就不负责了。这些兵役事务员,还有奸占人家妻子的。如象峰镇兵役事务员陈荣华,即利用权势奸占西街李某的未婚妻苏红枣,奸占后即把李某抓去充役。
征兵的弊端是如此的骇人听闻,征兵人员是如此的上下交争利,人民受兵役的苦难是那样的深重,逃避兵役的情况是那样凄怆,豪富的子弟几乎没有一人应征,而被征召的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甚至孤儿独子也不能幸免。像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叫人不愤控呢?1942年永春团管区司令何纪庭接到了泉州许多检举兵役舞弊情况的密告,曾亲自来泉处理。据说何纪庭来泉后,也曾微服到民间去了解,也曾审阅各乡镇造送的兵役名册,随后即命令晋江县国民兵团团长(县长兼)遍令城区各镇长传集各该辖内所有缓役的适龄壮丁,携带缓役证件到晋江县政府大礼堂接受检查,否则,决以逃役处理,依法严惩。那天到会的有一千多人,每人都携有公务人员的委任状和缓役的证件,依法均得缓役。至此。轰动一时的何司令来泉处理兵役贪污舞弊之事,也就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为什么会不了了之?那应该只有何司令和国民兵团团长才能知道了。其实在那个官官相护、上下交争利的时代,所有的案件不也都是如此的不了了之。且看国民兵团的书记洪伯阳,一家兄弟八人,都是适龄的壮丁,但并没有人一应征,既不出入,又不出钱,此事曾被密告于接兵部队,洪即托第十三处补训处中校团副杨献钦向接兵部队说情行贿,接兵部队对此也就不了了之。再者,如晋江县国民兵团分队长柯子碧,到南门外溜江村追捕自卫队队兵时,乘机抢劫队兵家属的财物,并贪污了赤金三两。队兵的家属通过了晋江县党部的关系,控告于省保密司令部,表面上对柯子碧虽然判刑三年,但监禁不久就放出来了。出来后又横行无忌,居然又在仙游踢死了一名怀孕的挑夫,虽然又判了刑,但不久又让他消遥法外,不了了之。再看44年,李振贯在大众报揭发西北镇镇长吴友根滥捕兵役新闻,越数日,李宅就被投掷二枚手榴弹;王冬青在泉州日报、晋江晚报揭发晋江兵役贪污舞弊和其他案件,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刘维驾因之怀恨在心,图谋报复,遂于同年农历七月初五日夜十二时许,密派县警察局督察何光耀与刑警队队员卢长寿埋伏在相公巷内王的住宅附近,等王回家时予以刺杀,幸未中要害,始免于难。像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当时的反动政府也是不了了之。
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征兵的罪行,我们知道的仅限于此,又很皮毛不够深入,希望关心地方史料的人士,予以补充指正。
(张一朋整理)
(原文载于1962年9月第七辑第34~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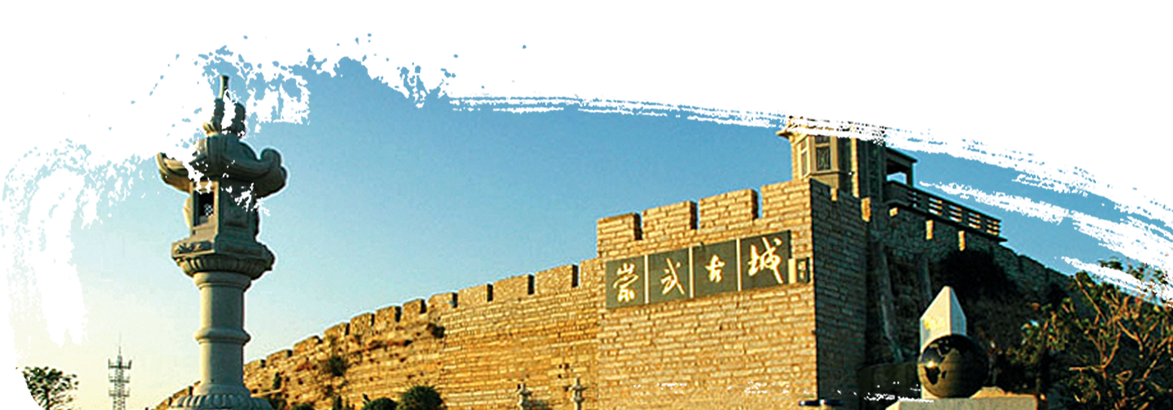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