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
发布日期:[2016-08-16] 阅读人:1637 字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计划之后,又于世纪之交启动了“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保护项目。中国提出申报的头一个项目是昆剧,于2001年列为第一批获得成功;中国的第二个项目为古琴,2003年也已通过。这种申报,两年一度,一个主权国家一次只能提出一个。那么,第三个项目是什么?现在,全国各地都很关注这个“世界性”的大事,都十分踊跃,有的地方全力以赴,千方百计争取金榜题名。泉州南音当仁不让,按照正常程序,已经进入候选项目。
人们也许会问,泉州南音有什么价值值得提出申请,凭什么资格去与众多竞争者的角逐?
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来观照一下泉州南音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特色。
泉州南音的特色,笔者在去年的一篇文稿中引用专家的论述和个人的看法,概括为五个字,即古、多、广、强、美。通俗地说,就是南音历史古老,曲目数量多,传播地域广,艺术生命力很强,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泉州南音历史悠久,被认为是千年古乐。其内容有“谱”、“曲”、“指”三大类,形成一个完整的音乐体系。现在初步收集统计,共有大谱十二套以上,散曲二千首左右,指套三十六至四十八套,总数有二千多首,经常在传唱的有几百首。这种优势和特色,为全国现存的各个古老乐种所没有。
大家知道,中国自汉代建立乐府以来,历代产生的音乐作品是不计其数的,但岁月流逝,大浪淘沙,能够传承下来或留在人民记忆中的,应该说是少之又少。但为什么泉州南音同样经历漫长的岁月和各种天灾人祸,于今还能保存那么多的曲目,尤其是在现代流行音乐铺天盖地的环境下,还能在闽南地区,港、澳、台和南洋一带闽南人聚居地广泛流传,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南音文化圈呢?从1977年开始至2002年,还先后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泉州、厦门、台湾等地,举办了十四次国际性的南音大会唱。专家们认为,这是因为闽南特定的人文环境,独特的方言口语和思想情趣所产生的一种文化。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样的,一方的方言口语和思想感情也养育了一方的音乐。因此,泉州南音千百年来,一直融入世界各地一大部分闽南人的血脉之中,牢牢地烙印在他们的情感深处。尤其是那些离乡背井、远渡重洋的海外赤子,对它更是难依难舍,永远挥之不去。许多长期生活在英语和当地语言环境中的闽南华侨,本乡本土的语言已渐淡忘,但只有当他们听到或唱起泉州南音来,他们才能重温本宗本族的母语,才能感受祖国与故乡的亲情与温馨。
以上说的只是泉州南音的优势和特色。但南音最主要的价值是什么?泉州能够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它的价值所在呢?
泉州南音最主要的价值,就是音乐学术界的专家所说的,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当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沨先生。他是在1984年至1986年间,于泉州筹备和成立“中国南音学会”期间一再强调的观点。当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黄翔鹏先生,在泉州“南音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有相似的提法。他说:“所有的乐种,都是历史的产物。……”泉州南音“它既与历史乐种有着诸种联系,本身又是当代犹存的乐种。有的同志把它看作历史乐种的一个‘活化石’,这话很有道理。”(《泉州南音艺术》P27-28,泉州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泉州市文化局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3)时过十几年,赵讽于1999年5月为吴世忠、李文胜合作用电脑编印的《南音名曲选》作序时,又再强调:“我曾经把南音称之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我的意思只是说,在南音的乐谱和表演中,仍然保存着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漫长时期的许多历史信息……。”(《南音名曲选》序一,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合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1)
赵老、黄老都是中国音乐学术界的泰斗,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言九鼎。可惜黄老、赵老已先后于1997年、2001年病逝,成为古人,不可能为南音的深入研究和保护及发展再作贡献了。
作为南音文化圈里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前辈权威性的结论,而不去探索黄老提出的南音乐种本身承上启下的脉络,和追寻赵老指出的“许多历史信息”。
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学术界的朋友和弦管界的弦友的共同努力。本人是门外汉,只是这十多年来在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工作,先后主持编辑出版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和吴世忠、李文胜用电脑制作的《南音名曲选》,主编出版了十五卷集的《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去年以来又承担泉州南音申报文本主要部分的撰写工作。在师友和同事的帮助下,对一些具体问题曾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现在整理出来,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笔者在学习赵老、黄老的有关论述之后,初步体会到,要探讨泉州南音的历史渊源,只局限于泉州一地来考察,是难以找出所以然来的。要真正认真考察泉州南音,必须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要放在整个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仔细探究,才可能理出头绪来。
中国有史以来的历朝历代,都有它的音乐,包括官方的祭祀音乐、宫廷音乐和大量的民间音乐。先秦的音乐文化就非常发达,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汉代宫廷设立专管音乐的乐府,民间的相和歌相当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发展为清商乐;隋唐继承相和歌、清商乐的优秀传统,朝廷设立管理音乐的机构,由七部乐发展至九部乐、十部乐。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是音乐爱好者,还亲自制曲。他们放眼世界,吸纳四面八方包括边陲或邻国的优秀音乐和音乐人才为其所用;李隆基还下诏把雅乐与胡乐相结合成为丰富多彩的燕乐。有了燕乐,再加上原来的大曲与法曲,又拥有多达二万余人的宫廷乐工队伍,这才构成中国音乐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期。晚唐、五代至宋初,这种强势已渐次减弱,随着一次次的战乱,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宫廷音乐似乎随之流失、烟消云散。南宋、元、明,南戏的出现和发展,所谓的四大声腔的形成和流播,辽阔的中国,好像只是戏曲的天下,纯音乐或与舞蹈相结合的音乐,似乎退至次要的地位,有的地方几乎绝迹。历代的音乐尤其是盛唐辉煌的音乐,只能从廿四史各代的《乐志》中去看它平面的记载,活生生的音乐原生态,已经无处寻觅。以致近代一些音乐史家,感叹中国音乐史是“没有音乐的音乐史”,或是“一部哑巴音乐史”。钱仁康先生在为叶栋著《唐乐古谱译读》一书作《序》说:“从宋朝到现在,听不到唐乐的声音,已经一千多年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5)
那么,中国隋唐以来丰富的音乐,真的是全部销声匿迹了吗?总体上说应该是这样的,但可能也有个别的例外。人们常说的“礼失求之野”,东海之滨的泉州,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应该是个属于“野”的范畴。恰恰是在这个“野”的泉州,恰恰是在泉州南音当中,人们惊喜地发现,竟然有汉晋、特别是隋唐音乐的许多重要遗存。正是有这些的重要历史遗存,专家们才敢断言,泉州南音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
现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泉州南音何以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
一、从南音现存各种形态来为千年古乐溯本追源
(一)泉州南音原名是源自晋唐的弦管
“泉州南音”的名称,已经叫了五十多年了。诸如“泉州南音大会唱”、“中国南音学会”、“泉州南音乐团”等,名闻遐迩,约定俗成。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也以“泉州南音”为名,要正名似乎不可能了。但五十多年前,泉州南音不叫南音,而叫弦管。这虽说仅是个称呼上的“更新”,无伤大雅,可是弦管一词,却大有来头。它确实与中国“古代乐种有着诸种联系”。史书记载,弦管之称,“初见于晋,但习用于唐,如’朝成一词,夕入弦管’”。在泉州,唐代泉州的第一个进士欧阳詹于唐。贞元八年(793)在东湖饯客,也写下“弦管饶拍,出没花柳”的名句,这决非偶然。而在五代的后蜀,“弦管诵歌,盈于闾巷”;《花间集》中,不但有“弦管、弦管,青草昭阳路断”的词句,而且有“听弦管,娇妓舞衫香暖”的描写,反映了词人眼前有弦管伴奏下的舞蹈情景。由此可见,“弦管”之称,晋唐以来都专指丝竹音乐。但奇怪的是,全国上上下下有许多古老的乐种,从来没见一个以“弦管”命名的。唯独泉州称“弦管”。泉州在半世纪之前的丝竹公会,就是由众多弦管班社组成的。弦管专指丝竹之音,别无分号。龙彼得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德国图书馆发现的明代刊刻的《新刊时尚弦管摘要集》,其曲目特点和语音方言,完全是泉州的,更充分地证明了“泉州弦管”具有悠久音乐历史的继承性。由于有了“弦管”这个名目,在很大程度上使今天称之为“泉州南音”的古乐,便可以与晋唐古乐“联系”起来。这一点,也为海内外一些资深的学者所认同。台湾吕锤宽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撰辑的一部指谱,就以《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为名,很具代表性。书名上加上括号的“南管”两字,乃因弦管传入台湾之后,为有别于“北管”而称“南管”,正如弦管传入鹭江之后称“南乐”一样,但都没改变其晋唐古乐弦管的性质。
总的一句话,源自晋唐的“弦管”,唯独遗存在南音之中,如果说是活化石,那它是其中“过于古老”的一种标志,不能不加以珍惜。
(二)自成体系的古老记谱方法
中国古代的记谱方法,有“减字谱”、“半字谱”和广泛使用的“工尺谱”。敦煌发现的二十五首古谱,也属于减字谱。泉州南音的记谱方法却有别于上述各种,黄翔鹏先生认为它“稍有略同而大有质异。”南音采用的是“工×谱”,以“×工六士一”,来对应“宫、商、角、征、羽”。以\/L○十氵等来标示琵琶指骨;以撩(、)拍(○)来规定时值。形成一个很完整很科学的记谱体系。《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3期发表南音研究者吴世忠《自成体系的福建南音工尺谱》一文指出,工×谱是与先秦的乐学原理相一致的。陕西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健正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著文指出:南音工×谱产生于汉代,早于“减字谱”、“半字谱”和“工尺谱”,幸存于泉州南音中。(《论工尺谱源流》,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工作通讯》,1985.2)有趣的是,上述敦煌发现的二十五首古谱,破译者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教授,他在《唐乐古谱译读》一书中说:“关于三群定弦与谱字译音,……故另参照福建南曲琵琶的弦音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泉州南音琵琶工×谱与敦煌唐乐古谱有某些相通之处。更重要的是,泉州南音的工×谱,一直是活着的,在海内外南音文化圈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发出美妙的音响,而不是像敦煌古谱埋在洞窟中,千年后才重见天日。
(三)汉唐古老的乐器只存活在弦管中
南音常见的基本乐器是琵琶、尺八(今称洞箫)、二弦、三弦、拍板。俗称上四管。还有四宝、双铃、木鱼、扁鼓等小打击乐器,俗称下四管。又有演奏“指套”时用的南嗳(小唢呐)、横笛,原先还有笙、云锣和、筚篥。
琵琶是中国主要的民族乐器,现在全国上下使用的都是竖抱的直项琵琶,通称“北琶”,唯独南音使用的是横抱的曲项琵琶,俗称“南琶”。这种琵琶一说是产于中原,一说是源自西域,汉代传入中原。现在已很少见,只能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的魏晋古墓中的图像和四川前蜀主王建的墓葬中找到它的踪影,或者去日本奈良正仓院参观遣唐使从中国带去的实物。但在南音文化圈,横抱琵琶是它的主要乐器,数以千计,而且许多乐器厂仍在不断地制作出产,供各地南音弦友采用。
洞箫古称尺八。它的规制很独特,有人认为它是以古代的尺寸而得名。但它的主要特点是采用竹的根部,十目九节,前五孔后一孔,而前五孔中必须有四孔放在上端的两节中间,不得有任何“越位”。这种也来自域外或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全国其他地方已很少见。国内也只能在魏晋和唐、五代的墓葬中找到它的图像,而实物也只有几件保存在日本奈良正仓院。1984年日本的一个团体为了寻找尺八的历史渊源,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最终在泉州如愿以偿,激动万分,其后多次组团参加泉州的南音大合唱,并把日本“精竹会”改名为“泉州会”。
另外一个重要历史见证,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两件明代德化烧制的瓷尺八,南京博物馆也收藏一件。这说明,弦管在四五百年前的山城瓷都也十分盛行,因此才有如白玉般的瓷尺八的问世,并成为国家珍宝,于今又刊载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二弦和三弦,专家也认为是晋唐以来奚琴和三弦的遗制。
除此之外,在晋江东石民间,尚保存有“”和“筚篥”。“”是拉弦乐器。《中国音乐词典》记载,“”产生于唐代,宋代盛行,改称为“轧筝”。晋江当地也许谐音叫“床”,只保存一件,据称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另一件已是破烂不堪,不能使用。而筚篥,是古代龟兹传入中原的乐器,史书上多有记载。泉州南音早期的“”与筚篥,可能与笙、云锣等先后被简化。与筚篥如今比较孤独地保存在乡村,说明它的历史存在,益显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拍板,是中国古代音乐掌握节奏的一件重要乐器。原先是六片,以后也许是与五音相对而改为五片。泉州南音也应该有个六片简为五片的过程。其重要证据在泉州开元寺。
泉州建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泉州开元寺,堪称为泉州古代南音乐器博物馆。上述南音的主要乐器琵琶、尺八、二弦、三弦、拍板和小打击乐器共十二件,全部掌握在大雄宝殿木雕斗拱十二尊飞天乐伎手上。与它媲美的,是在大雄宝殿后面的甘露戒坛。这座建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的全国仅存三大戒坛之一的藻井结构的佛教古建筑物,在其屋架的斗拱廿四尊飞天手中,同样有南音上下四管的各种乐器。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经与敦煌的初唐和中唐壁画比照,可以大胆地认为,它们恰如是古印度佛教音乐神鸟《迦陵频伽舞》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盛唐的《霓裳羽衣乐舞》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建于南宋嘉熙二年至淳佑十年(1238-1250)的镇国塔(东塔),在须弥座的四十幅浮雕中,有一幅“天人赞鹤”,竟然有一“天人”在吹笛,一“天人”双手执六片拍板为之打撩按拍。这是七百五十多年前的遗迹,十分宝贵。这个塔座石雕的拍板为六片,与飞天木雕拍板为五片不同。正好印证了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说的:“古无拍。魏、晋、五代,……始制为拍。古用九板,今六板,或五板。”(《曲律》刊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P118,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11)这说明,魏晋以来六片或五片的拍板,泉州开元寺都有遗迹。如果说,大雄宝殿和甘露戒坛的木雕飞天南音乐伎,可能在唐宋建寺时就已经雕成,后来也毁于火灾,明代的两次重修或大修时加以恢复,或是晚明郑芝龙重修时的首创,尚无定论。那么,东西塔则是建于南宋,“石写”的历史自然更为确凿无疑。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多元形成的盛唐音乐与来自天竺、龟兹等地的佛教文化,或先或后传入泉州,开元寺和双塔的前身,是始建于唐垂拱年间的,这就是个重要标志,其影响是不间断的,并一直延续至宋及明代,所以“桑莲法界”不论建塔、修殿,都为音乐留下重要的位置。二是佛教寺院,尤其是泉州开元寺,在世代老百姓的心目中,其地位是崇高和神圣的,而南音同样是崇高和神圣的,所以其木雕和石刻的乐器先后都登上大雅之堂,长存至今,令人称奇。
(四)南音的演唱有严格的礼仪与规制,保存了中国古代“礼乐”的遗制与古士君子遗风。
1、演唱排场:左尺八(今称洞箫)、二弦;右琵琶、三弦,唱者双手持拍板而歌。这种形制,专家认为与汉相和歌“丝竹更相和,执节而歌”的形态是完全一致的。
2、演唱曲目的程序:开场先由尺八或南嗳和上、下四管吹奏“指套”的某一曲,随后则按开场的“管门”选唱若干散曲,最后奏大谱结束。这种安排,是唐大曲的演奏遗规。
3、演唱礼仪:南音界崇奉后蜀主孟昶为乐神,每年春秋二祭,十分虔诚;南音三十六套“指套”中,有专门一套用于祭郎君的曲和词。兄弟社团互相交往称“拜馆”,所拜的就是“郎君”。南音的正规演唱,一定要先在郎君像前焚香,顶礼膜拜,然后才整弦演奏。在演唱中,唱员或乐员要替换,也有严格的规矩,双方交接拍板或乐器,都要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凡此种种,说明泉州弦管保存了中国古代礼乐的遗风。
二、从新发现的南音典籍,来查寻历史例渊源
泉州南音既然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必然会有古老的曲文或曲谱存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我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在编纂出版了十五卷集的《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基础上,又启动了“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计划。我们编校出版的两部书,将作为申报文本的“典籍依据”。一部叫《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一部叫《清刻本文焕堂指谱》。
这两部书的底本,都是海外孤本。明刊戏曲弦管的三种选集,在中国大地上早已绝迹,但却尘封在英国和德国图书馆数百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英国牛津大学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发现,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调查研究,撰写了长篇论文,1992年自费以《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为名在台北出版;我们收到他的赠书,并征得他的同意,翻译了他的论文第一章和三种明刊本的书影,于1995年以同样的书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印1000册,已经发完。龙先生不幸于2002年5月过世。我们经过龙夫人的同意,征集了他那篇论文共五章的全部中译稿,连同三种明刊本的书影和校订本,汇编成一部500多码16开本的大书。
第二部是清咸丰年间成书的《文焕堂指谱》。长期以来,弦管界对这本指谱,只闻其名,不见其影。据信闽南地区只有残本,没有全本。我们获得台湾朋友赠送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本子的书影,全部用电脑输入,部分还翻译成五线谱。也编成一部500多码16开本的大书。
为支持这两部书的出版,中共泉州市委书记施永康撰写了序言。同时,我们把两部书的清样送到北京,请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章,和该院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田青,分别写了序言。他们高度评价泉州南音的历史价值和两部书出版的意义。这两部书已于2003年底以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两部书(简称为明刊本和清刻本)的底本,因绝无仅有,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一是明刊本有弦管曲词选集三本,其中一部分还附有音乐拍号。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的《音乐学论文集》,认为《明刊三种》是20世纪所发现的民间传统音乐史料的第一部。与现存有限的弦管史料比较而言,它是迄今发现出版年代最早的弦管曲词选集。而清刻本指谱,也是所有正式出版工×谱曲集年代最早的版本。二是有了这两部明清正式出版的弦管史料,就使中断已久的千年链条,找到两个中间环节,可以承上启下把它连接起来。如果说“传统是一条长河”,南音史也是一条河流。那么,有了这两部书,就有助于使这条淤塞的河流流动起来。
在编校这两部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书中蕴藏了不少重要的音乐历史信息。这些信息与其他有关史料结合起来研究,让我们对南音悠久的音乐历史和多元的文化特征,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明刊本收集了弦管散曲曲词二百七十二首(其中重复者十四首),雄辩地证明了弦管散曲在明代已经大量存在,而且相当成熟。而清刻本收集“指套”三十六套,大谱十二套。许多内容是与明刊本一脉相承的。这样一来,南音的三大构成部分:指、谱、曲,都有了明清时代的正式出版物,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和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来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南音的曲目由指、谱、曲组成。大量的是散曲,二千首左右,其次是指套,三十六至四十八套不等,谱最少,十二套至十六套不等。那么,这么多的指、谱、曲是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呢?现在看来,肯定不是,一定有先有后。指套由同类型的散曲组成,曲早于指,应该不成问题。但有的学者认为大谱晚于指套形成,或者把“大谱”与“指套”等量齐观。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了一本插图本《中国古代音乐史》214页称:“谱,即大谱,为曲牌联缀的套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3次版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也认为“谱……每套包括三支至八支曲牌”。这恐怕都有些误解。
现在我们有了明刊本和清刻本,可以清楚地看出,南音的指、谱、曲三大类:“谱”的历史最为悠久,“曲”其次,“指”是在曲大量涌现后形成的,故为最后。
那么,上引两书的著作者,前者为什么把“大谱”与“套曲”等同起来,后者也认为“谱”是由若干曲牌组成的呢?这大概是可供研读的正规出版的“大谱”向来稀少,比较通行的似乎只有林霁秋的《泉南指谱重编》。但这部《指谱》经过他的重编修改,已经失真,以致造成许多误导(林霁秋关于弦管曲目某些故事来源的臆测,龙彼得也提出批评。可参看《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一书。)
祖籍同安的林霁秋,于民国初用了十八年时间,在鹭江编了六大本集的《泉南指谱重编》,功不可没。但他也许出于好心,把指谱中的许多名目都加以改动,以致弄得面目全非。比如十二套大谱,清刻本的《三面金钱经》、《五操金钱经》、《八面金钱经》,林霁秋把它改为《三台令》、《五湖游》、《八展舞》,名目虽是美化了、诗化了,但却把它原来属于佛教音乐的性质全部抹煞了。又如《走马》,林霁秋改为《八走马》,后人也许感到《八走马》文理不通,再改为《八骏马》。又如《走马》原本分为八节,以一节、二节至八节标示,朴实无华,林霁秋却分别加上所谓“骅骝开道”、“玉骢展足”、“赤兔嘶风”等八个小题。企图用八分多种的一首乐曲来表现八匹骏马奔走的形态。这当然是不可能也不必要,违反了纯器乐曲的“反文字性”的特点。博导田青在《净土天音》(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11)一书中(P176)说:“一切企图用语言’描述’音乐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现在,我们以原貌把《文焕堂指谱》输入电脑,并连同底本的书影一并出版,就可以正本清源,擦去林霁秋加上的油彩,还大谱以历史的真面目。
那么,清刻本这十二套大谱的历史真面目是什么呢?
(一)大谱开头的三套都是《金钱经》。之所以分为“三面”、“五操”、“八面”,乃是每套当中有三节、五节、八节之故。林霁秋的修改,不但全部改去《金钱经》的曲名,而且全部改掉了各节的名目,冠以〔升平颂〕、〔簇御林〕、〔赏宫花〕、〔满江风〕、〔浪淘沙〕等曲牌名。难怪上海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把大谱与套曲等同起来。三套《金钱经》原来各小节的名目是<大双清>、<喝哒句>、<番家语>、<折采茶>、<夜游折双清>等等。这些名目,恰恰保留了佛教音乐的重要历史信息。其中的<番家语>,自然使人想起当年中原人对域外音乐和语言的称呼,而<喝哒句>该是<哈达句>的谐音,不言而喻与藏传佛教有关。至于那个乍看文理有点不通的<折采茶>、<折双清>中的“折”字,却可以为上引田青《净土天音.佛教音乐的华化》的文章提供一点佐证。该文说:佛教东传初期伴随口头传入的佛教音乐曲词有三千多首,而被曹植记录下来的只有四十二首。曹植记录的不是曲辞,而是用《汉书补注》所说的“声曲折”——“以曲线状声音的高低婉转的原始的、直观的、不甚精确的示意谱。”如果笔者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上引的<折采茶>、<折双清>等,也许都与早期佛教音乐有密切关系。这些魏晋至今的重要音乐历史信息,被“重编”者一笔抹煞,诚属可惜。
(二)清刻本的《阳关三叠》,分十节,名目为“阳关、一叠、一关、二叠、二关、三叠反关、中关、尾关、尾叠”。但林霁秋却把它改为《阳关曲》,小节名目改为“渭城曲、折柳吟、一叠、进酒歌、二叠、阳关曲、三叠”。这显然又是画蛇添足,扭曲原貌。《中国音乐词典》称:“《阳关三叠》,唐代歌曲,今存琴歌谱。歌词据王维的……诗并有所发展。诗中有’西出阳关无故人’,又重复三次,故名《阳关三叠》。唐宋以来,曾有多种唱法,现存琴谱三十多个版本……。”现在,我们如果消除林霁秋的修改,还以原来的真实面目,那么,南音这首大谱也可能为《阳关三叠》保存一个唐宋版本。
(三)清刻本十二套“大谱”,都是属于“虚谱无词”的纯器乐曲,其性质是否与南宋词人姜白石在乐工故书中发现的“商调《霓裳曲》十八阙”同一性质或有某些相似之处,有待专家们去研究比较。
(四)唐大曲的结构,据宋《碧鸡漫志》说,“凡大曲有散序……入破……实催……歇指、杀衮始成一遍”的记载,近人把它解释为“音乐情绪、节奏的发展大致为散-慢-中-快-散的脉络,则唐大曲不会离开这个构架。”以这个观点来对照南音的大谱,仔细聆听“四、梅、走、归”或其余大谱的演奏,其音乐情绪、节奏发展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不能说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应该是同宗同祖、一脉相承的。
(五)盛唐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唐玄宗所作或润色的《霓裳羽衣曲》。这首名曲早就佚失,在宋代就已经找不到了。南音指谱《趁赏花灯》中有首以<舞霓裳>为曲名,外地有个音乐团体特地派人来泉州请弦友演奏,想找回当年的《霓裳羽衣曲》。但结果当然不是。原来这是个误会,《舞霓裳》是《拂霓裳》的谐音。《拂霓裳》是唐教坊曲名之一。指谱保存的不是原版的《霓裳舞衣曲》,如果是唐教坊名曲,意义同样非同一般。
(六)音乐学术界长期来一直想找回《霓裳羽衣曲》,结果都是落空。后来发现白居易当年聆听这首名曲所作的-长诗《霓裳羽衣舞歌》,长达八十多句。(《全唐诗》P1673,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9出版)从中多少可以窥见这首绝响名曲的音韵,可惜白居易只是用诗而不是用曲谱记录这首曲,后人自然无法了解其美妙的旋律。但实录的诗篇,总会留下一些历史信息的。现谨摘其长诗第一部分的八句于下。
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
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
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
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原自注: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
读了白居易这段诗和他的自注,笔者顿然省悟,大谱的《走马》的结束句,不正是有个“歇拍”——“却收翅”和由“工”音突升至“亻工”的“长引声”吗?过去我这个门外汉听《走马》,不明白“工”音为何突升八度为“仜”,误以为是吹奏中的所谓“闯管”,原来却是保存了《霓裳羽衣曲》的特征。经请教弦管行家,他们说,大谱中的《起手板》、《百鸟归巢》都是如此。那么,有了这个发现,如果经过行家验证认为言之有理,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向音乐学术界的同仁宣布,倘若要寻找遗失一千多年的《霓裳羽衣曲》,不妨到南音的大谱中来探微寻踪,相信类似“却收翅”、“长引声”的遗音,决不止是这一些。
明刊本戏曲弦管选集三种,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历史信息呢?
(一)明刊三种为泉州南音古称“弦管”找到根据。在明刊选集中,前文说的有一集名为《新刊时尚弦管摘要集》,明白无娱,可以为证。如果没有这部明代弦管选集,我们就无法证明泉州弦管之称,至少是自明代传衍至今已有四五百年;当今的南音也无从与晋唐的“弦管”联系起来考察,而且也无法在流播地区分析源与流的历史痕迹。
(二)明刊本收集的弦管曲词和戏文,从中可以找到三十多出戏的痕迹。但不要以此而认为泉州南音是产生于宋元南戏诞生之后。如果这样认为,必然造成本末倒置。须知在明刊本中有大量的曲词并不全是来自戏曲。我们曾费很大精力不断寻找那些曲词的剧目归属,结果是徒劳无功,原因是许多曲词是“无主事人”,分明不是从戏曲中游离出来的,而是晚唐、五代、宋时文人创作的曲子词。如《金井梧桐》、《月照芙蓉》等等,都是文绉绉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它们最值得宝贵的地方,是中国自唐宋以来创作的曲子词可以说数以千万计,但能够传衍千百年、于今仍活在音乐中的,恐怕只有泉州南音这些古老的散曲。
(三)明刊本中的三种散曲选集,应特别留意的是《百花赛锦》,集中那些以〔双调〕、〔背双〕和〔越调〕为调名的散曲共五十多首,而这三个调名——〔双调〕、〔越调〕和〔背双〕,非同寻常,《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告诉我们,它们的调名源自《唐燕乐二十八调表》。似可这样说,一千多年前的盛唐燕乐,在明刊的弦管选集中有它的遗存,而且延续至今,在弦管中还不断地传唱。
(四)明刊本的曲词,全都采用闽南方言。更准确地说,是用泉腔闽南方言写成的。其中大量的借音字,乍看起来令人费解,但只要用泉州方言音韵去加以解读,就能找出它的本字。而其本字,有一部分则是比较生僻的古汉语;其中有些被认为是有音无字的“土话”,经考证却是十分古老而又文雅的文字。而这些古汉语组成的词汇,往往在《词源》、《辞海》中都找不到。足见它们早就在语言海洋中沉没了。前年在泉州师院举行的全国古代汉语研讨会,许多专家认为闽南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这是事实,但要分别对待,因为现在的闽南方言,有的被普通话所“同化”或被“硬译”,已经走音变味;有的又被外来语和时代流行语所渗杂,面目全非。要找比较纯正的闽南方言,只能从古旧的闽南方言里面去寻觅。可惜以前没有录音机,古人怎样说话无从稽考。幸得泉州南音和南戏的各种刻本、抄本,或多或少可以填补这个空白。这些刻本、抄本,大量的借音字,正好把那些古汉语的读音记录下来。再者,泉州弦管戏曲界有个严格的传统,就是强调“照古音”唱念道白。这种唱念道白的标准音,则以历史上泉州府治所在地即当今鲤城区的语音为标准。邻近乡镇、县城带有“乡腔”的人士要学唱曲演戏,都必须“正音”。更不用说距离较远的兄弟地区。何乔远在《闽书》中称:“(龙溪)地近于泉,其心好交合,与泉人通。虽至俳优之戏,必使操‘泉音’,一韵不谐,若以为楚语。”可见在弦管戏曲中读音是十分讲究的。正因为这样,泉腔弦管戏曲,就起了录音机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个因由,泉州南音之所以叫泉州南音,就是由泉腔方言决定的。音乐是语言的延伸,要寻找古老泉腔方言中的古汉语活化石,明刊本以及清刻本同样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富矿,有待去发掘。
总之,上述明刊本和清刻本的发现和出版,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找到一份有力的佐证。为“当代犹存乐种”与“古代乐种”互相沟通提供了一座宽阔的桥梁。
三、以“音乐随人走”的理念,来研究南音的历史成因和乐神崇拜
从南音原来名称、记谱方法、古老乐器或音乐本身及其典籍等方面,都可以说明泉州南音是来自中原的晋唐古乐,或者是晋唐以来的中原音乐在泉州的宝贵遗存。
对此,人们也许要问,偌大的中国,中原古乐为什么不是传留在中原,或传存在近距离、交通方便的黄河上下、大江左右,反而传至远距离、交通不便的千山万水之外、东海之滨的泉州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历代中原人南移说起。从严格来意义上来说,泉州是个移民社会。现在的泉州人,应该说绝大多数是中原移民,闽越的原住民恐怕不会太多。西汉初年,闽越、东瓯互相攻伐,又叛服不常。汉武帝派兵平定之后,索性下诏,命令军吏把悍逆的闽越人迁徙去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到了三国孙权时,闽越人丁有所发展,才增置郡县。入晋以后,五胡乱华,晋人南迁,福建迎来大批晋人。唐《十道志》称:“清源郡(今泉州),秦汉土地。……晋南渡,衣冠族多萃其地。”唐《闽中记》称:“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也。”
南迁入闽的人自然会带来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因而泉州才出现晋江、洛阳、青阳这些带有晋人色彩的江河和乡镇的名称。
音乐是随人走的。八大姓晋人是否带来清商乐,不得而知。但隋书音乐志记载:“永嘉之寇,尽沦胡羯,于是乐人南奔。”那么,这些南奔的乐人,有否奔入泉州?没有确凿的史料,不敢妄断,但也不能排除。社会发展到唐代,泉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有“市井十洲人”的诗句,可见已是国际性的城市了。盛唐歌舞音乐的辉煌,在泉州不可能不波及。唐贞元八年(公元792),泉州第一个进士欧阳詹几次在东湖饯客,都有歌舞活动的记载。而“弦管饶拍,出没花柳”,更是直接点到弦管音乐的主要特征了。稍后,即唐大中(宣宗847-859)时,永春名进士盛均作《桃林场记》(当时永春尚未成县,称桃林场,属泉州府南安县),有这样的描述:“俗阜民安,度日而笙歌不散”。(盛文收入《唐文萃》。据余承尧《说弦管》。)
再一次中原人南移是晚唐时期。黄巢起义,中原大乱,出现五代十国纷争的局面,河南人王审知统治闽国,其侄子王延彬当泉州刺史二十六年(一说十七年),懂得繁荣经济、发展外贸,赢得一个“招宝侍郎”的称誉。他“多艺,工诗歌,颇通禅理。”“日亭午方起,雅能为诗,辞人、禅客谒见,多为所屈。宅中声伎皆北人……。”《十国春秋》这些记述很有意思。这个刺史多才、多艺,又是个玩家,家中养了不少北方来的艺人。王延彬和这些人应该都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有辞人或禅客要求领教领教,都不是他的对手。别看他懒散得很,睡到日照午才起床。原来正如他的诗所写:“两衙前后讼堂清,软锦披袍拥鼻行。”闲来无事,他就在泉州(现西郊)建立“招贤院”(该地名仍存,叫招贤乡、招贤大队或招贤村),把处于中原战乱中朝不保夕的文人雅士,大量招募到相对安定繁荣的泉州来,其中著名的有诗人徐寅、黄滔等,又有“唐学士韩偓挈族来奔”。这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温陵”安身之后,饱暖思娱乐,于是王延彬在云台山建立清歌里,分设歌院、舞榭、琴房,并在不远的南安山区设立狩猎场。当时,清歌里唱什么曲、弹什么琴、跳何种舞,无从稽考。但王延彬“宅中声伎皆北人”,不能不引起今天弦管界的特别关切。这些北人老死在那儿?其后裔又在何方?他们的声艺留给谁家宅院?从当时的情势看、他们避乱而来,既来之则安之,绝无回去之理。可以想像,王延彬所招来的,不论是诗人还是声伎,都必然对泉州的音乐文化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后,隐居仙游的诗人詹敦仁应留从效之邀到泉州来,耳濡目染,写下了“万灶貔貅戈甲散,千家绮罗管弦鸣”的诗句,折射了当时泉州社会的歌舞升平,其中也许有王延彬当年播下的种子在开花结果。如果我们发挥想像力,对照南唐《韩熙载夜宴图》描绘的歌舞晚会场面,清歌里的或王氏宅中的歌舞情景,大概会是同一档次的。
有了这两次中原人和中原文化先后进入泉州,才造就泉州弦管的逐步形成。有的专家认为,五代前后是泉州弦管的奠基形成期,应该是可信的。
再一次中原人人泉,是宋靖康之后,南外宗正司由镇江迁入泉州,一定居就是漫长的一百四十七年,最后人丁发展至三千余人。他们是皇族,而且是赵匡胤的嫡系,对泉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必然是巨大又深远的。特别是他们历来养尊处优,原先就拥有大批乐工舞伎,外迁定居泉州之后,当然也不能免。史书记载,属于正司级的宗正司,可以到京城“教坊”请乐师来教授音乐歌舞。南外宗正司有这个权利,何乐不为?宋亡后,其后裔在修家谱时,比较清醒地总结了家族的经验教训,曾立下了不准在府中“夜饮、妆戏、提傀儡以娱宾”的家训。足见他们先辈为沉沦于骄奢淫乐而国破家亡。由此反证了南外宗正司的音乐戏曲活动是相当繁盛的,对当时泉州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宋亡元兵入城,宗子多数被杀,其他人役四散。五代时有两句诗:“梨园弟子偷曲谱,白头人间教歌舞”。这对于从南外宗正司四散的乐工舞伎也适用。他们别无其他谋生技艺,不在民间教歌舞将何以为生?这些年,泉州当地和外地的几位研究者,都从泉州弦管、梨园戏和傀儡戏的优秀传统艺术中,注意到它们都各有严谨的规制,成熟的体系,艺术上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传承上师道尊严,训练有素。因而才能保留那么多的艺术珍品,从而世代传承,成为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认为,这只能是由那些有权有势有财力的宫廷教坊或王侯家班造就的。不则,如果只是纯粹跑江湖卖艺糊口的民间戏曲,往往是朝不保夕、自生自灭,不可能有那么深厚的艺术积累和文化含量。当然,这只是推论,还有待找到可靠的史料来作证。
以上说的是三次中原人和中原文化,由北向南迁移对泉州产生的直接影响;其间还包含着一次横向的间接的转移,和一位历史人物对泉州音乐文化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就是四川的后蜀及其蜀主孟昶。众所周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照理说东海之滨的泉州,是不会也不可能与蜀地有什么交往的。但奇怪的是,泉州的弦管甚至某些独特的语言,不但与蜀地的音乐与语言都有微妙关系,而且其后蜀主孟昶,还被泉州众弦友恭请来做乐神,崇拜上千年,甚至享受了与文圣(孔子)与武圣(关羽)同等的待遇——春秋二祭。
这是为什么?史料介绍,天府之国有极丰富的音乐文化积淀。特别是唐代的两次皇帝逃难都入川,一是唐玄宗避安史之乱,二是唐僖宗避黄巢之乱。后宫嫔妃和梨园、教坊的乐工都随之入川,于是盛唐以来的优秀音乐歌舞都在四川有大量的积淀,加上孟昶父子专心致志的经营,后蜀就积蓄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和作品。中国第一部曲子词《花间集》以及花蕊夫人的词作,都在成都成书并传向全国,成为传世之作。这些事件发生在万里之外。与泉州关系不大。但历史的发展变化和音乐随人走等客观规律作用,却造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转移和交融。
史书记载,宋军迫降后蜀之后,孟昶和花蕊夫人等被押去汴京。其后,孟昶精心培养的乐工,被遴选一百三十九人进入宋初建立的教坊,他们占教坊人员总编制的三分之一,成为传承盛唐和五代音乐的骨干。
后蜀广政二十八年(965),孟昶一行到汴京,宋太祖把花蕊夫人夺去,赏给孟昶一个秦国公的封号,赐宴后七日而卒。花蕊夫人悼念孟昶,画像偷偷祭拜,被太祖发现,她谎称为“张仙”,皇帝难得糊涂,认可了事。当时神仙道化盛行,连皇帝都承认花蕊夫人画的肖像是神仙,自然会得到他原来臣民和故旧乐工的认同与崇奉。这也许就是孟昶崇拜的起因。宋史说赵匡胤皇帝只当了十六年,就让位给弟弟,退居二线享清福。及至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宋太祖嫡系的南外宗正司,经过辗转迁入泉州。宗正司中当年那些被宋太祖选入教坊的后蜀乐工的后裔,自然会把原先的音乐文化及乐神崇拜的传统,一并带入泉州。
正是南外宗正司的定居泉州,泉州几乎成为南宋的陪都;正因为宗正司中有蜀国乐工的后裔,才使后蜀的音乐文化和宋教坊的艺术传统和乐神崇拜,与泉州嫁接起来。也许这就是泉州弦管界郎君崇拜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这样认为,这种崇拜便是无源之水,是永远无法解释的。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孟昶这个历史人物是否值得崇拜,是否够资格成为弦管的郎君先师?大家知道,戏曲界一般都是崇拜唐玄宗(老郎)和雷海青(田都元帅)的,因为一个是“梨园”事业的开创者,一个是铮铮铁骨的乐师。崇拜有理。而崇奉孟昶,恐怕只有泉州弦管界,着实令人费解,因为孟昶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又是一个失败的小君主,似乎无啥可取。但据《十国春秋》记载:孟昶当政时,“是时蜀中久安,斗米三钱,……金币充实,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宴社会,昼夜相接。”由此可见,孟昶治下的蜀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治安都不坏。尤其是大街小巷都有弦管与歌声,这种景象一定会让泉州人感到亲切。当孟昶合族及官属投降后,“发成都,由峡江而下。”十分凄惨,但“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十国春秋》的作者,对此还加了一段评论:“史言后主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借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这正好印证了他自己的感叹:“吾父子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
由此可见,孟昶还是有值得崇敬的地方。引用一句老话: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对孟昶也是合适的。弦管人对他虔诚的祭拜。决不会无缘无故。也许如史书所言,他当时确实有恩于国人,有益于弦管。所以他的“国人”和他的乐工,因怀念故主,才会产生这样一种带神话色彩的崇拜。
以上种种,有些说法是笔者的“大胆假设”,有待今后继续“小心求证”,但有一点,把泉州弦管的历史渊源与孟昶崇拜连结起来研究,应该是不会离经的。
总的说来,泉州如果不是接纳自晋代以来的三次大移民,如果来者只是“打工族”,而不是士族、皇族,他们带来的如果只有兵器和农具,而没有晋唐以来的优秀文化。那么,今日的泉州也许是另一个样式,也许就不可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南音之都和戏曲之乡。因此可以说,泉州是得天独厚的。是特殊的历史机缘赐予的,全国以至于福建的其他地方,也许就是缺少或没有这种机缘,所以才缺少或没有这类的历史文化积淀。具体地说,千百年来是那些日常需要而且有可能享受比较高级的音乐文化的人,才有条件去精雕细刻音乐作品,去编制完整的体系,才造就了泉州弦管,才在泉州保存了晋唐以来灿烂的中原音乐文化。而当这种晋唐以来的灿烂音乐文化,在中国其它地方几乎都消失了,都找不到了,有的早就无影无踪了。唯独泉州却有幸地保存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这就可以视为奇迹,这就显得特别珍贵。本文开头提到的赵老、黄老等前贤们把它们称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重要的是这个“活”字),那是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
千年历史既然把中国一部分仅存的活的音乐文化留存在泉州,并由泉州传向四面八方,这无疑是泉州人和所有弦友的福分。同时,保护好这份民族文化遗产,也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参考书目:
龙彼得辑《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胡氏拾步草堂藏本《文焕堂指谱》
吴世忠、李文胜电脑编制《南音名曲选》赵沨《序》
中国南音学会《赵沨先生与泉州南音》及其他资料
黄翔鹏《“弦管”题外谈》
林霁秋《泉南指谱重编》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田青《净土天音》
赵为民《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
余甲方《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
叶栋《唐乐古谱译读》
沈冬《南管音乐体制及历史初探》
吕锤宽《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音乐词典》
中华书局《十国春秋》
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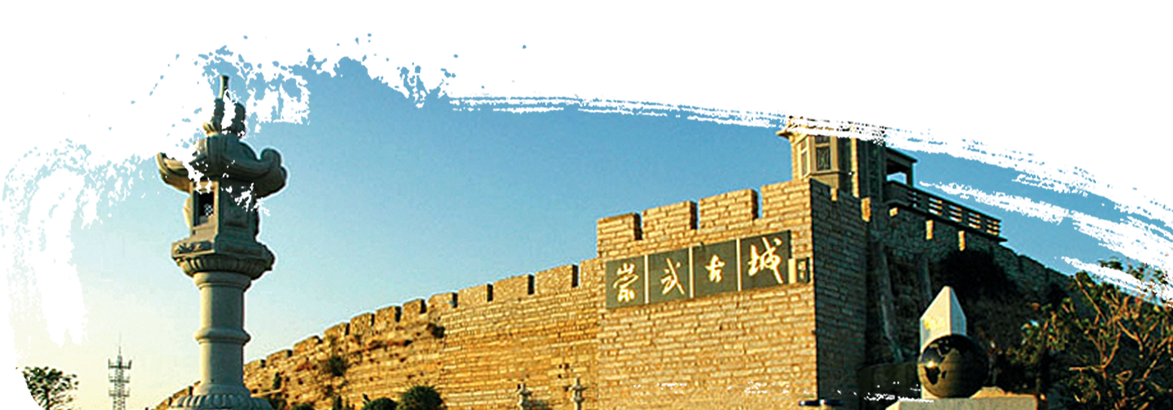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