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兼容闽南文化的主导研究方向
发布日期:[2008-04-15] 阅读人:1637 字号: 河洛文化兼容闽南文化的主导研究方向
陈 水 德
内容摘要:闽南文化区域概念的习惯性使用,招致异地同质文化族群的质疑。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本质一致,但河洛文化超越地域局限,能够为异地同质文化族群普遍接受和认同。河洛文化内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底,外连闽南区域海洋文化之特色,尤在起始根脉上显现文化的本质性,有利于两岸同胞原始文化之认同。故以河洛文化兼容文化的主导研究方向,将具较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河洛文化 闽南文化 同质文化 两岸同胞
闽南文化的研究在目前情势下,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困惑问题,即除厦、漳、泉三地的闽南之外,在同质文化的其他区域遭遇到了较普遍的质疑。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地域为概念所概括的文化内涵显得过于狭小,不足以在最大层面上完整地容纳全部同质文化的内涵。而在历史上,却早有另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河洛文化概念,则足以涵盖闽南文化概念的实际应用。故此,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应明确推动这一概念习惯性使用的转变,有效确立该领域文化研究的真正主导方向。正如客家文化非以客家的生活地为称呼所普遍使用的文化概念一样,得以完整和恰当的转述和表达。
一、以闽南地域为概念研究文化的局限性
闽南是一个区域性的地理概念,闽南文化即为该区域性的文化概念。长期以来,闽南文化已被习惯性地广泛使用。但问题在于,闽南文化的同质内涵并非仅限于闽南厦、漳、泉三市区,而是广泛分布和存在于其它许多地区。如龙岩的新罗区和漳平县,广东的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和雷州半岛,海南的汉族地区和台湾的绝大多数地区;此外在浙江、江西、广西、江苏等省区,也分散有部分的县、乡、镇、村;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为主的省外华裔河洛文化的闽南人聚居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陈水德(1956—),汉,龙岩人,黎明职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区等。据统计,在我国境内约有闽南文化同质人种5000多万人,占汉族人口的4.6%左右。在全球范围内约有8000多万人。[1] 可见,闽南的所在地仅是闽南文化同质族群存在的最集中区域,但并不等于该同质文化的全部存在范围。近年来,以闽南文化为称呼所进行的文化宣传和研究活动,已越来越受到同质异地人的质疑,致使自身同质文化出现不应有的认识裂痕与情感隔阂。对此, 提出河洛文化兼容闽南文化的主导研究方向,将有利于在同质文化的全部存在范围内达成最广泛的共识,以促使该领域文化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民族社会和国家利益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化的生长必以一定的区域为载体和活动范围,离开一定的区域,文化的生长就难以实现。文化是人类聚居的产物,但文化的存在却不以固定的区域为范围,文化是人类活动极其活跃的内因子,可以无限地广泛地渗透与传播,尤其是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系文化就很难会受制于某个文化区域的局限,而是能够广泛地与不同文化交融在一起。闽南文化的成长与实际发展过程,同世界诸如犹太人、拉丁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同操英语的许多国家人一样,都最终成为文化混同的局面,却非局限于某一地域概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故大凡有更大发展的人种、民族和民系,多数都能超越地域局限使用和构造自己的文化概念,成为跨区域跨国界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文化内涵。我们提倡河洛文化兼容闽南文化的概念使用,其基本意义也正是如此。
二、以河洛文化为根脉溯源的本质认同
河洛也是一个与区域有关的概念,从原意上讲是指中原地区的黄河与洛水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顾名思义,河洛文化即是指黄河与洛水流域的文化,概指中原文化或中州文化,即中华民族的原生文化。但从现在来讲,却又偏偏非指河洛故地的现有文化体系,而是特指始于晋代以来,不断从以河南固始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所传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特别是闽南区域所形成的文化体系,一般习惯地称呼闽南文化为河洛文化。若从本质上讲,始于宋代而同于中原地区所传入闽粤赣交界地的客家文化也属于河洛文化。但历史上却遵从了先来后到的原则,先来的河洛人尊称后到的客家人为“客”,而后到的客家人虽然明明也知道自己也源自河洛中州,却偏偏称呼先到的人为河洛人,而习惯地接受了自己为“客家人”的称呼,由此表明两种不同民系的文化区别。而历史上把河洛人叫得最响的不是别人,也恰恰是客家人和当地的原住民(“蛮獠”后传的畲族人)。[2] 故河洛人就由此形成了新的一大民系。
“河洛人”也称“河老人”、“福佬人”、“华老人”、“阜老人”等,皆为一音之转的偕音字。中州人南下形成河洛民系,在学界中早有定论,多数学者都认为,北人南迁入闽主要经历了三次移民浪潮:第一次移民浪潮以“晋人南渡”为历史标志。西晋末年,中原暴发永嘉之乱,洛阳世家大族遭到屠戮,幸存者纷纷南逃,其中入闽贵族虽遍布建州、福州和泉州,但主要集中在泉州的晋江流域。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晋江,在县南一里,以晋之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多沿江以居。”以后成为闽南的重要祖先之一。其中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大姓为入闽衣冠的主体。今泉州丰州附近发现有不少两晋南朝的墓葬及其器物,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从总体上看,第一次南渡的河洛人在数量上依然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闽地的人口结构。有记载,西晋闽中全境不过8600户,到南朝宋时更减至5885户,其中主要是居泉晋安郡的人口4300户。人口虽少,但重要的是晋人南迁,带来了大量先进的中原封建文化。中原成熟的语言、宗教、技术、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传至晋江流域,对于“傍海荒服的”的闽地原始族人来说无疑将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使闽地的传统文明有了新的发展,河洛人及其河洛文化也因此被奠定下来。
第二次移民浪潮以“开漳圣王”为历史标志。这一次移民浪潮从人口数字和时间来看,都存在问题。从唐总章二年(669)开始,陈政、陈元光父子先后两次率府兵入漳,人数多达7千多人,可考姓氏82个。但奇怪的是,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在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当时连整个漳州的总人口都达不到这个军队的数字。如徐晓望认为:“盛唐的开元年间,漳州人口只有1690户,后来泉州的龙溪被拨入漳州,漳州人口才上升到5千多户。”所谓“后来”,最迟在天宝年间(741—755)以前,“漳州人口为5346户,17940口”[3] 但根据郭启熹引《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认为唐建中年间(780—783)漳州总人口仅6336人,汀州仅15995人。[4] 二人所述人口数和时间数都有差别。假如龙溪人口并入漳州是在建中后,则二人说法可以相通。还有一地点问题,二人记述也出现相悖情况,很值得注意。徐晓望认为陈元光家族祖先曾定居于福建的仙游县,攻打漳州时,陈政父子并非从北方率兵南下,而是直接在泉州一带招募士兵南下作战,最终开创漳州。[5] 这样史实的记述,实源于《福建通志》卷十五的记载:惠安县北有陈政故宅。[6] 而郭启熹则明确引《漳州府志》称:陈政、陈元光父子“命将分军镇戌置行台于四境,四进躬自巡逻,其一在泉之仙游乡(今龙溪县)松州堡,上游至苦草镇”。[7] 可见,郭启熹所指明的该历史问题上所记述的“仙游”所在地,并非指今天的仙游县,而是属于漳州境内的一个乡。二者所述的不同根据有待进一步考证。无论如何,陈政父子进入漳州后,种种资料的确表明漳州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此一来,陈政父子入漳则似乎不能构成移民浪潮之说。其中的隐情可能存在两种:一是由于战争惨烈,双方均伤亡太重,以致漳州人口数锐减;二是若果真如徐晓望所说,陈政父子的军队主要是招募于泉州地带,那么就可能是在漳州战事之后,其军队的大部分人都回到泉州老家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此次移民浪潮虽然在短时间内漳州的人口并没有实际的增加,但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却极大地促进了漳州人口的迅速增长,[8] 故此次移民浪潮同样足以说明“开漳圣王”的历史事迹是河洛文化来源的另一重要历史时期。
第三次移民浪潮以王潮兄弟入闽为历史标志。唐末以来,黄淮流域战乱不已,又有大批中原人南迁。其中最典型的是光、寿二州移民入闽,使河洛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唐末光、寿二州刺史王绪举兵起义,率5000兵士南下,王潮兄弟加入军中,从“略浔(九江)赣走汀州”[9] 进入闽南。王绪渡江陷漳州后被王潮所杀,王潮兄弟掌控全军。首先占领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5年后王审之攻陷福州,于是占领全闽。当时,光寿移民将士加家属约计4万多人一起南下,占据全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极大地提升了河洛文化在闽的地位,及其为以后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总之,溯源河洛文化之根脉的南传,一在于人本身的血统不变的自然迁转,这是根本之根本。从三次中州移民南下来看,每一次都十分集中地与河南固始人有直接的血亲关系,以致极其完整地形成了同一血缘的文化基础,所以文化的认同,首先是根脉的认同。徐晓望证实说:“闽人的族谱有80%以上籍贯河南固始,闽中历代名流,也有80%以上籍贯固始,这种说法即使其中只有一半是可信的,也足以说明古代河洛文化对闽文化影响极大。”[10] 这种族源的认同,是最坚实的本根认同,是河洛文化南传的真正本质所在。所以,河洛文化所概括的本源意义较之闽南文化所概括的地域意义更为准确和恰当。二在于表明河洛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承关系上。实际上它不仅是传承,而是同一整体。河洛文化本来就是中原正统的民族传统文化,只是从中原地带迁移南下传播,并得以更大发展和保存而已。所以,在民族传统儒、道、释等思想文化的主导下,南下河洛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戏曲艺术文化、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都完整地体现和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涵。这从以泉州为代表的河洛闽南人屡屡能够扬名于科考仕途上就可见一斑。据《泉州教育志·科举》统计,自唐贞元至清末期间,泉州考中进士共有2543人,状元先后有10人,这样的仕进成就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是难以想象的。而科考仕途又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得到最顽固捍卫的一块官家阵地。加上,闽南地区还被广称为“海滨邹鲁”和“朱子过化”之地,也足以说明河洛文化的民族传统本质。当然,文化的内源基础所传承的传统本根性,还远不止于此。闽南方言、戏曲南音等能够完整地保留晋唐时期的中原品质,依然足以充分说明河洛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直接延续和传承。正徐晓望先生所指出:“闽南人大多以固始为籍贯,说明他们将自己的‘根’定在了北方的中原区域,这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民族鉴定上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只要有了这一点,就奠定了他们是汉人的基础。再从文化继承性来看,闽南人文化的主流,是中原文化的延伸。闽南方言最接近于唐宋暑期的中原语言,这已是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闽南人的文化观念,也是以发源于中原的儒家思想为其根源,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成为他们基本的行为准则。可见,闽南人当然是汉民族的一部分,虽说闽南人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但是地方性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影响到闽南人的文化共性。”[11] 因此,河洛本根文化是闽南人的共性文化,也是所有南下河洛人所共有的文化,但绝非是仅限于闽南地区所共有的文化。故从文化本质溯源上看,河洛文化概念的普遍使用无疑更为超越和妥当。
三、彰显河洛文化主导研究的闽南特色
河洛文化源于中原,为民族文化正宗所传。因此,自晋代以逐渐所南传的河洛文化,在多领域多层面保留和传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最深层地表达了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诸如理学的兴隆,易学的发达,道学的脉传,语言的原声保留,戏曲艺术的宫廷特色,科考仕进的价值判断,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民族一体性和传承性等,都深深地烙下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灵印记。然而,河洛文化南传之后,在新的地域环境里和传播的广大范围,受到了许许多多不同新文化因素的广泛影响,而必然发生新变化,故最终使河洛文化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中原文化,而是具备了自身非常可贵的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新生文化要素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源自南下海滨之地所引起和形成的一系列新文化形象与内涵。其中,以地域性所彰显的闽南特色为典型。
虽然认为,河洛文化广为传播,但她的主要集中区域是在闽南。闽南必然是研究河洛文化的主阵地和主要的力量所在,离开闽南地区的河洛文化研究,无疑将失去根本和基础,所以突显闽南区域的文化范围与内涵,是河洛文化研究的最大特色。基于闽南区域范围的特色认识,河洛文化在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显然大量地充实和注入了富有闽南地域特色的新内容。其中主要有,河洛文化的海洋色彩、海上贸易的主体经济内涵、华侨华人的开拓精神及其贡献等。尤其是海洋色彩,就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里,还广泛地体现在生活领域、思维领域、艺术领域和宗教领域等多方面的内容里。比如河洛文化的宗教特色,就突出地体现了其海洋性。妈祖海神以及各种宗教所突出的海洋性,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明显地凸显了海洋文化的重大特色。在泉州几乎所有的神灵都可以成为海神的一分子。
因此闽南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闽南的特色是大海的特色,而从河洛到闽南,到大海,成为不可分的文化整体,即河洛文化居于闽南而体现了大海特色。所以河洛文化的闽南特色,实质上是河洛文化的海洋特色。大海是广阔的包容的,所以河洛文化在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形成了无限的丰富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等文化格局。即以民族原生态的河洛文化为本原,以闽南地域为文化存在的主要空间载体,以海洋活动为文化滋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托,以及包容古闽越文化、海外文化和各民系文化,并不断地伸向海峡两岸、港澳和南洋异邦及世界各国,形成河洛文化的全过程和完整形态。因此,研究河洛文化基于闽南地域,不仅是显示文化的特色所在,更是表示文化的生命所在。结论是,闽南区域的海洋性是河洛文化的主要特色,研究河洛文化的根在中原,基础却在闽南。
四、河洛文化完整体现了两岸文化的同质性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不仅是指台湾文化与闽南文化乃至全闽文化的同一性,更在本质上与民族传统中原华夏文化的完全同一性。但近些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受到岛内台独政治势力的严重压制,“台独分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断地制造文化混乱局面,企图割裂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性,大搞所谓本土文化和台独文化,否认台湾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性,妄图通过“去中国化”的政策获得“台湾文化”的独立地位,其用心极其险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对此,我们认为在当前两岸复杂的情势下,有必要特别突显中原河洛文化的南传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以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的本根认同,从思想上和文化上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国家的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河洛文化的南传,首先是中原河洛种群的大量南移,构成了以闽南地区为主要聚集地的河洛民系的广大分布局面。包括河洛血亲南传至闽南,至福建,至南方的许多地方,至海峡对岸,至南洋海外等广大地区。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河洛血亲是构成台湾族群的主体。台湾族群,无论是从血缘上看,还是从种群上看,或是从民系上看,都直接源自中原河洛的正宗脉系。据统计,“台湾的汉族移民中,福建人约占83.1%,其中泉州籍约占44.8%,漳州籍约35.1%,汀州、龙岩、福州等约3.2%;粤籍移民次,约占汉族人口的15.6%;其余1.3%,为其他各省的移民。” [12] 再根据“人类学家陈奇禄先生1985年的统计,台湾祖籍闽南达75%,使用闽南话更高达80%以上。”[13] 总之,“自明清开始,福建向台湾移民,近几十年的几次统计数字表明,台湾居民中80%以上是福建人。” [14] 在台湾的人口中,无论是福建移民,还是其他省籍的移民,无论是河洛人,还是客家人,都是源自中原的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即便是古代台湾的“夷越人”,在族源上也与大陆特别是与福建有着直接的关系。[15]
由于族群的人口来源所致,台湾至今所用语言主要有两种,一是汉语普通话,二是方言闽南话。汉语普通话,是大陆通行的官方语言,同时也是台湾地区的官方语言,在中国境内及其世界各国华人居住区内广泛使用。台湾民间由于闽南人占据绝大多数,故所用地方语言普遍通行闽南话。这两种语言,无论是汉语的官方语言,还是闽南语的民间方言,都是中华民族自身绝对纯正的语言种类。如今有“台独分子”要在语言上做文章,企图用闽南话代替普通话做官方语言,这是十分可笑的行为。因为闽南话本身就是河洛语言,是晋唐时期中华民族所普遍通行的官方语言,是十分正统正宗的原始汉语言,“台独分子”的语言图谋,不正好证明了台湾同胞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大家庭吗?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十分警惕“台独分子”的可笑企图,决不能让台独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阴谋得逞,不能让河洛文化的闽南语言成为他们实现台独的工具。
在共同族源与人口构成的基础上,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民族大文化,特别是中原河洛文化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表明两岸社会的全部基础和内容都存在着不可离异的内在坚实的联系性。有关这些问题,两岸学者基于大量的史实均有过十分确凿的论述。如有学者认为:福建文化在台湾广泛传播,形成了与闽人相同的价值观、传统思维和强烈的寻根意识。“闽人移居台湾后,虽然在台湾建家立业,但他们的根毕竟在大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代代相传,逐渐沉淀为强烈的寻根意识。”于是有台湾同胞在村庄的命名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浓烈的寻根意识,令人无比感动。[16] 又有学者从大量的事实来说明,台湾与福建在语言、习俗、民间信仰、戏曲艺术、科举教育、相互任职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共同性与共通性,证明台湾文化的民族本根不可置疑。[17] 还有学者列举闽台两地在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文学创作、方言与戏剧音乐、民俗与信仰、海外华人与侨乡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彼此互融、互通与互惠的内在联系,是民族传统文化在两岸地区的直接贯通与传播的广泛表现。[18] 总之,有关台湾文化的民族本根性的学者论述已十分充分,足以证实台湾文化源自中原河洛文化的基本事实,故笔者在此不另作细论。
闽南文化以地域为基点突显河洛文化,河洛文化超越地域概念涵容闽南文化,二者实为同质文化,没有根本区别。河洛文化以固始族源为起始,是在逐渐南传闽粤等地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庞大的民系文化体系。如今我们倡议河洛文化概念的普遍使用,不仅将更有利于弥合闽南地区以外其他海内外广大地区的同质文化,确立明确共同的寻根核心目标,形成具有同一文化向心力的更加强大的民系族群和聚合形成广大同根同源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且也将更有利于台湾同胞文化根源与血亲族源的起始认同。直接展示河洛文化的明确根底,使文化认同与血亲族源的认同,就不再会象过去那样仅停留在闽南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而是可以直达起始文化的河洛源头上,广泛表达两岸文化的根本同一性。总之,我们认为,任何文化的存在离不开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但任何文化同时又必将具有无限传播的本质特征。当某种文化较稳定地存在于某一地域范围内的时候,以地域为概念的文化称呼是可行的,但如果当文化无限扩张与传播的时候,同时存在有超越地域的文化概念,则显然以此概念为广泛称呼和使用更为恰当。如客家文化超越地域性概念的通用,就远较于该文化局限于某一地域概念的使用更为恰当。故在闽南文化的基础上,重新统一河洛文化兼容闽南文化的认识,确立河洛文化代替闽南文化所普遍使用的概念,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1][4][7][13] “闽南文化发展研究”课题组.闽南文化现状与发展初探[J].闽南文化研究,2005,8:2、10、11、14.
[2] 参见郭启熹.龙岩史海钩沉[M].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2004,13.
[3][5][11] 徐晓望.北方移民与闽南人的形成[J].泉南杂志,2005,11;28、28、37.
[6][8] 漳州市委、政协.开漳圣王[M].福建:海风出版社2005,8、12.
[9] 杨修田,光州志,卷5,武功列传(M),光绪版,1880刊。
[10]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台文化研究[A].徐晓望.论河洛文化南传与闽文化的崛起[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7.334.
[12][16]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台文化研究[A].唐文基.林国平.闽台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7.15、15.
[14][18]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台文化研究[A].方宝璋.方宝川.略论中华文化的地域性与闽台文化的特色[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7.52、53.
[15]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台文化研究[A].卢美松.闽台古代种族渊源[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7.85.
[17]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台文化研究[A].杨彦杰.闽台文化关系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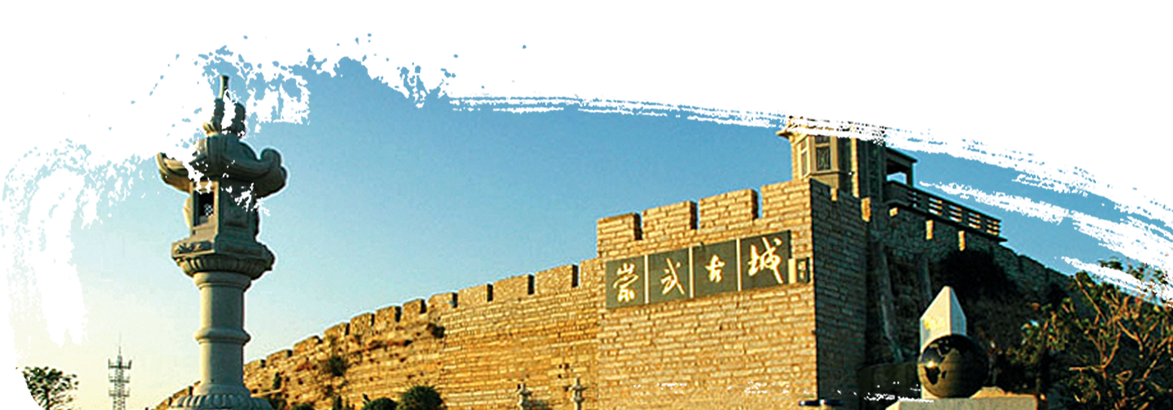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
闽公网安备 35050302000182号